聲明: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連線Insight(ID:lxinsight),文/張霏,編輯/李信,授權轉載發布。
短視頻廣告還有金礦可挖嗎?
問題的答案,不能只看活得光鮮亮麗的甲方品牌公司,水面之下隱藏的不同角色從業者們,比如廣告代理公司、視頻制作方、演員,才有更真實的直觀感受。
“泡沫被嚴重擠壓,行業越來越內卷,我們這些處在產業鏈底端的中小創業者生存很難。”李涵作為短視頻信息流廣告的內容制作方,在圈里摸爬滾打兩年多,最終還是選擇離開這一行。不只是李涵,他身邊的所有同行朋友以及上游廣告代理商們也都在尋找新的賺錢機會。
只是,現在很難有一門生意能像短視頻信息流廣告那么容易賺錢——門檻低、超暴利、商業邏輯簡單。
一些草根們的暴富神話主要源于短視頻信息流廣告的興起。
2017年之前,信息流廣告還是以圖文為主,但短視頻興起后,用戶們每刷幾條短視頻,幾乎就會出現一條廣告,內容簡單,制作也稱不上精良。一些視頻下方標記著明顯的“立即下載”或“立即購買”提示按鈕。

短視頻信息流廣告,圖源抖音APP
正是這種場景立體化、劇情套路式的短視頻表現形式,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用戶意識不到這是短視頻信息流廣告,看得津津有味。殊不知他們看的每一秒、點擊每一下,背后廣告服務商們口袋里的錢正源源不斷地增加。
根據Quest Mobile數據,2021年,在各種廣告形式中,短視頻信息流廣告占比從2020年上半年的24.6%增長到2021年上半年的30.8%。表面來看,圖文信息流廣告的體量被壓縮,視頻逐漸成為主流廣告形式,這對品牌主來說是好用的營銷方式,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有越來越多大量的下游服務商創業者闖進來。
多位信息流廣告從業者向連線Insight坦言,即便到現在,大部分廣告的毛利也能超過60%甚至更高。早期入局者更是用各自的方法都分到了一杯羹,可能是年入百萬,甚至賺了幾千萬,實現了財富自由。
“批發”式生產、小團隊運作……肉眼可見,這是一門令人上癮且門檻極低的生意,自然會吸引越來越多人入場。
這也讓李涵越來越感覺這個行業“很沒有道理”,“這一行業賺不賺錢,并不是看從業年限和年齡,可能就是偶然的一個機會,你就在這一行業站穩了。比如現在很多小創業團隊但凡能接到一個信息流的甲方大客戶,一兩個月的時間就能開始賺錢了。”
行業有多暴利,紅利期一過就會有多殘酷。競爭導致的是大部分紅利向“頭部”集中,加之各平臺規則變嚴格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大量信息流服務商的利潤空間被大大壓縮、經營難以為繼。
于是,批量裁員、倒閉、被逼轉型等寒潮,也在信息流廣告服務行業出現。
信息流廣告服務商們走到了行業的十字路口。“我很簡單,不奢求爆款作品、不談理想、只求能夠養活自己的團隊,留給我轉型的余地。”這是李涵的想法,也是行業內其他準備離場的從業者共同的心聲。
曾月入數百萬,一夜暴富成現實
無門檻、可觀的行業利潤,讓不少人一夜暴富,他們久久沉浸在“伊甸園”里,不愿醒來。
李涵也短暫體驗了一把身價百萬的感覺,那時是2020年疫情期間。
2020年,信息流廣告行業進入洗牌期,在不少從業者看來,也是屬于草根創業者的最后一波紅利期。當時疫情導致影視行業的項目停工,短視頻平臺卻迎來了日活的大幅增長,短視頻廣告也迎來紅利期。大量短視頻制作需求,讓眾多掘金者涌入行業。
電視劇、網綜、模特等影視行業的各個崗位人才,開始不斷進入到這個曾不被外界關注但高毛利的新興行業中來,也有大量學生利用業余時間提供兼職服務。
李涵則是這波入行大軍的其中一員。因為之前有省級電視臺的從業經驗,很快他就融入新圈子。
“您好,請問您需要做信息流廣告的推廣嗎?我們可以給您拍視頻,短平快,曝光效果好……”李涵通過地推,拿到了第一筆來自本地某款社交軟件的10萬元訂單。
那時,他的公司名下只有他自己一個員工。但沒關系,廉價、速成是這個產業鏈最顯著的標簽。
起步有多容易?李涵提到,“當時我就是一個‘二道販子’。先自己寫好腳本,每條50多個字,也不費事,六分鐘就可以寫完一條劇本。我當時總結了一個基礎模板,比如說前1-3秒會設一個懸念,中間部分講故事加產品,最后引起用戶的共鳴,引人深思、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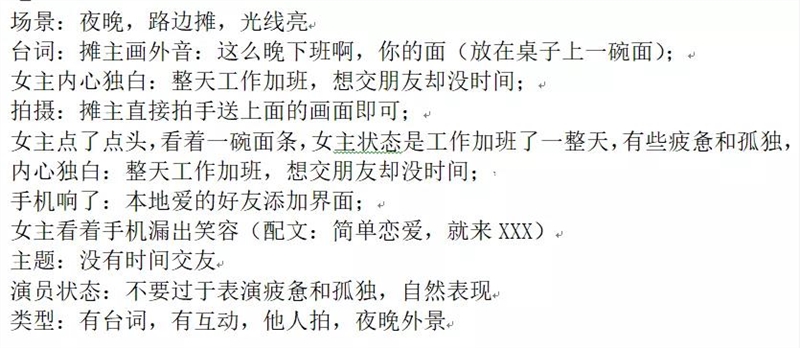
短視頻信息流廣告的腳本模板,圖由受訪者提供
制作成本有多低?李涵告訴連線Insight,“我們基本上所有的片子都是按照這個模板來寫的,然后再填充一些所謂的爆款因素,接著以30塊錢/條的價格,找女大學生拍攝,最后以70塊錢/條的后期價格,將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外包出去。基本上,只要我的腳本沒問題,最終成品也不會返工重做。”
靠著快速復制,批量生產的方式,一條短視頻的成本被壓縮到幾百元。而當時的視頻也容易通過,李涵發現“只要經過剪輯,不是完全相同的畫面,平臺算法不會判定為抄襲。”
就這樣,李涵第一筆10萬訂單的生意幾乎沒費什么力氣,就凈賺7萬多。這讓他嘗到了甜頭,隨著客戶逐步增多,他開始組建自己的四人團隊——兩名剪輯師,一位攝像師,李涵負責編劇兼導演。
這個行業有三種結算方式,一種是一口價,比如成品拍完后,不論最終投放效果如何,用一定金額價格直接買斷;第二種是底價+分成的模式;第三種模式就是零底價,只拿消耗分成,即視頻制作方先做作品,之后根據品牌方投放的廣告金額抽取一定分成。廣告消耗金額越高,提成就多,若投放效果不佳,可能一分錢也拿不到。
李涵此前接的一口價單子中,有五六個視頻最終跑出上千萬元金額的消耗,這可是罕見的大爆款。如果按照第三種結算方式,視頻創作者平均能拿到1.5%的提成,也就是他每條至少能拿到10多萬。因此一條視頻起量越大,賺得越多。
自認為掌握了爆款密碼的他,不再甘心只接一口價單子,他開始接純消耗的訂單。
“最開始幾個月做得還不錯,連著爆了十幾條視頻,每條視頻都消耗了上百萬金額,當時自己一下賺了一百多萬。”收到貨款的第二天,李涵帶著淘寶上定制的爆款符就去了千佛山燒香,“還找大師開了開光,掛在公司門口。說來也怪,從那之后,團隊做的視頻再也沒有出現過爆款。直到臨近年底反而賠了20多萬,我才反應過來不能再做純消耗的單子了,當時差點兒連員工的過年工資都沒發出來。”
如今,每天能灑出幾百上千萬廣告費的甲方變少了,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曾在短視頻廣告中激戰最酣的在線教育行業集體大幅縮減廣告投放。
今年5月,據《晚點LatePost》報道,猿輔導、作業幫、好未來等幾家頭部在線教育企業在字節跳動廣告投放的廣告金額約300-400萬/天,而去年暑假,僅猿輔導一家公司,一天就在字節跳動投出超過3000萬元的廣告額。
自雙減政策開始后,猿輔導、作業幫、學而思網校、高途四家頭部網校的大班課、啟蒙課程業務也基本停止了信息流廣告投放。
這個行業龐大而脆弱——商業模式圍繞著甲方訂單運轉,這注定了下游的被動,所以當上游訂單減少,整個行業轟隆隆的生產線就會一起受影響。
躺著賺錢的日子過去了
時間回到11月初的一個深夜,濟南歷下區的一間工作室只有噠噠作響的鍵盤和鼠標點擊聲,光聽聲音仿佛只有機器在工作,但這卻是李涵與剪輯師們一起趕“片子”的日常。
臨近“雙11”,各個品牌方都指望在這一節點沖業績打個翻身仗,信息流廣告做預熱宣傳必不可少,壓力自然會傳導到產業鏈下游。
李涵作為老板,把所有能派上用場的員工都用上了,雖然他的團隊只有7、8個人。現在,他已經和員工連續加班7天7夜,這很瘋狂,不過今晚就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把成片交給甲方客戶手中了。
今年下半年,整個工作室的主要營收全指望這幾天了,他不敢松懈。“都不回家休息,我當時就天天給加班的員工點薯條炸雞當夜宵,買了幾張行軍床鋪在隔壁空辦公室,給每人準備一件軍大衣,暖風機呼呼吹整宿,誰累了就躺去休息。全部人都睡在一個屋,鞋一脫,屋里那股味兒你都難以想象。”
李涵也向連線Insight解釋:“沒有一個信息流的公司是不加班的,信息流行業本身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無一例外。何況是遇到雙十一,大家都很拼。”
但與去年雙十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發現,上游廣告代理商放出的高價單越來越少了,去年他接到的單子大多數都是2、3000元/條,今年基本都是5、600元/條。“我沒有辦法去明確地講短視頻信息流的紅利期是不是過去了,因為現在截止到目前為止,人家頭部公司依舊做得很好。”
北京的廣告代理商羅選的感受略有不同,“其實現在大部分廣告代理商生存狀況也不太好,尤其是互金與K12在線教育都‘團滅’了,大家倒閉的倒閉,裁員的裁員。這兩個行業是我們代理商的頭部品牌主,依靠著這兩個行業發展紅利,有些廣告代理商在短短一兩年時間就成為百億流水的行業頭部公司。但是現在大變天啦,冬天來了。”
不同于李涵只有兩年的從業經驗,羅選屬于廣告行業的“老人”。
2018年,羅選辭去在網易從業10年多的廣告相關工作,成立了一家廣告公司,主營業務便是做短視頻平臺的信息流廣告代理。“‘雙減’政策沒頒布前,我最大的客戶就是教育行業,然后是游戲、電商、金融,這幾個都是市場體量非常大的賽道。”
彼時,為了獲客,K12在線教育平臺不惜花高營銷費用投放信息流廣告。因此,不少廣告代理公司專注于在線教育行業。
羅選向連線Insight透露:“北京的代理公司多數都是做教育行業為主,所以今年下半年在線教育行業遇冷后,影響最大的就是北京這些廣告代理公司。業內有家頭部公司,今年上半年做到60億流水,去年做到了100億流水,在線教育行業就是他們的大客戶。”
在雙減政策沖擊波下,這家頭部廣告公司自然也未能幸免。羅選感嘆:“他們北京整個總部都裁掉了,所有人都沒留下。”當然,羅選自己的公司也受到重創,“自己一半數量的員工都被裁掉了”。
在線教育倒下了,游戲、金融廣告也被政策嚴格監管,多位短視頻信息流廣告代理商感覺自身處境已經很危急了,他們認為“廣告公司賺的錢開始不多了,我們只能轉變思路,把那些高成本的單子直接砍掉,賺錢的訂單我們自己留下。”
其實在線教育行業的相關政策下發之前,羅選為了減少開支,已經單獨組建了一個5人小組,專門生產短視頻信息流產品,也就是和李涵做的工作相似。“一二百條的小單子,自己團隊完全能承接得住;只有上千條短視頻廣告的大單子或者需要大制作成本的高難度劇情廣告,才會分成好幾批下發給不同內容創作方。”而像羅選這種操作的廣告商,在業內已經十分常見。
一二線城市的廣告代理商們的日子不太好過,從前者手里接活的內容創作方自然也撈不到什么油水。
成交價和廣告需求量,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減,下游不得不向尋找新出路。張默帶著自己的內容創作團隊不再死盯著短視頻平臺客戶,試圖轉戰傳統電商平臺,但掙扎了幾次,他便放棄了。
“淘寶的視頻服務商更多,我們反而會被客戶白白利用。”張默發現,不少服務淘寶商家的同行,為了拿到客戶資源,自愿把自家腳本賤賣到1元/個,“更有甚者愿意給客戶‘免一送四’,意思是免費給商家做5條短視頻廣告,最終也不一定達成合作。”

腳本一元一個,圖由受訪者提供
張默提到,他們這個以95后年輕人為主的40多人團隊,打造過一些爆款視頻,每個月至少有大幾百萬的收入,“當然這是以前了。”自他長期服務的大客戶先后受政策影響,縮小營銷投入后,躺著賺錢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當大品牌方開始減少廣告投放費用,廣告代理商為縮減成本自建視頻創作團隊,利益鏈最下游的第三方內容創作方尤其是中小腰部公司自然感覺如李涵一樣,“高價片子少了很多,低價單子賺得越來越少。”

集體進軍直播帶貨
一邊是少量頭部廣告商依然日進斗金,一邊是分不到羹的中小玩家賠本賺吆喝,有人選擇躺平,但大多數人開始逃離、轉型。
李涵讓一半數量的員工專門研究如何在抖音直播帶貨,并且他“花了1萬塊錢,去學習其他公司是如何做直播帶貨的,然后讓對方老師對我們的直播間進行一對一調整,相當于花錢買了一份課程。”
巧合的是,張默和羅選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直播帶貨這一條路。
選擇轉型直播帶貨這一方向,是因為直播帶貨所需要的角色與內容創作團隊幾乎是相同的,他們不需要再費時間搭建新班子,只需招聘主播就可以了。

雖都選擇直播帶貨這一方向,但切入方式卻大不相同。
編導專業出身的張默希望先做內容賬號,再變現。他喜歡做原創作品,這讓他之前短視頻廣告的產能受限,其他團隊一天至少能生產15條短視頻,他最多10條。而且和追求品牌質感的傳統廣告不同,信息流廣告的目的是轉化用戶,并不追求原創,這讓張默團隊很吃虧。
現在短視頻信息流廣告不好做了,他也有機會好好研究如何做內容賬號了。“最近探店達人比較火,我打算一起孵化多個賬號試試看,商業化變現路徑可能是通過直播,幫商家賣優惠套餐或者限時秒殺之類的。”
同為廣告代理商的劉圭,此前有MCN機構和品牌運營等多重角色的從業經驗,對直播帶貨的機制較為了解,他決定試試做商家的代運營。先做帶貨培訓課程,像李涵這種就是他的客戶——新人主播們在此時入場,都渴望殺出一條血路。
不可否認,隨著直播電商滲透率的明顯提升,在直播間買東西變成了越來越多用戶的日常。人社部等部門發布互聯網營銷師新職業信息,也讓帶貨主播成為了正式工種,做主播培訓已經是一個新消費熱點。
除了主播培訓,劉圭自己還作為“投流師”,負責客戶直播間的流量投放,拉動直播間的GMV,這一工作內容和短視頻信息流廣告有些共通之處。
2020年上半年,抖音上線了一款只面向電商客戶的直播間商業化投放流量工具——巨量千川,電商客戶可以通過在“巨量千川”上投放流量,增加直播間的觀看人數,從而提高GMV。這其中有一種為“feed直投”的投放形式,它會截取正在直播的“直播間”的動態畫面,通過信息流的方式投放到抖音首頁中,從而吸引正在刷短視頻的用戶進入直播間。
“不過對于商家來說,現在盲目投流,只怕會虧本陪跑。”一位MCN機構從業者告訴連線Insight,在抖音剛切入電商時,通過“巨量千川”在直播間投放10萬的流量一般達到100多萬的GMV,但今年不好做不到這一效果了。
但興趣電商依然是商家們不敢錯過的方向。大多數玩家們不過是在同一生態里,從一個角色換到另一個角色。上述從業者繼續補充道:“現在布局抖音電商,對于相關從業者來說,既是進攻也是防守。防守是擔心興趣電商成為電商業態的一種主流形式,進攻則是玩家們需要這種新的模式去構建業務增量。”
只是沒有一個風口是永遠存在的,泡沫的生成和破滅是必經之路,“后臺一開,鈔票自來”的短視頻廣告造富盛宴或許快要結束了。重要的是,暴風雨過后,能在一片蠻荒當中找到新玩法的玩家,才有可能繼續創造新造富神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