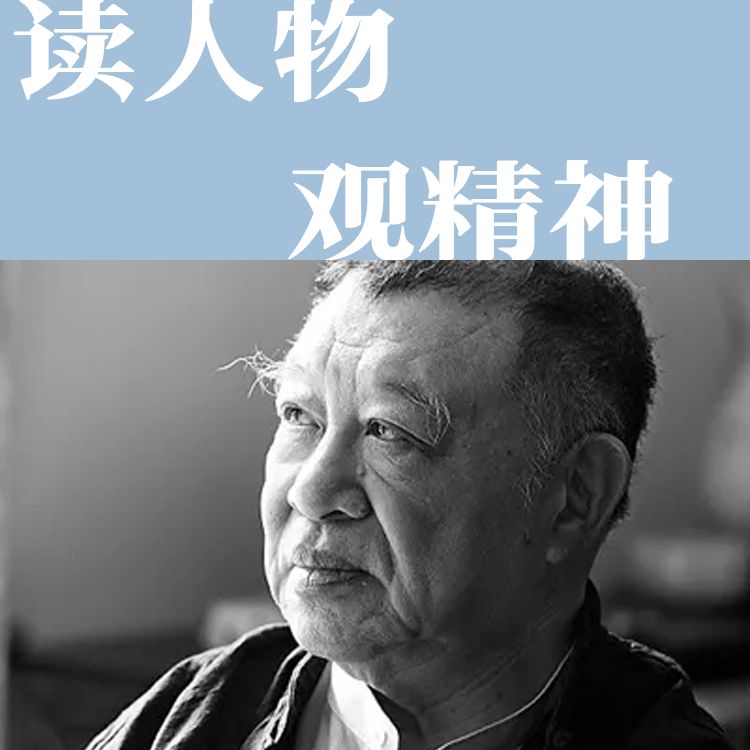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年近9旬的許倬云接受訪談節目《十三邀》的專訪。
在節目中,主持人問許老“如何應對很大的精神危機”。
他引用了詩句“時人不識余心樂”來表達自己的心境,然后溫柔而堅定地說:
“你是什么樣的人,就有什么樣的人生。即使是清貧的生活,也有直接、現實的快樂。”
這份豁達,讓人想起王爾德那句話:
“我們都在陰溝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那仰望星空的人,必定內心藏著生生不息的夢想與希望。”
是啊!生活實苦,但只要心中有光,就會無懼人生荒涼。
落紅點點,若消極看待,只會看到“零落成泥碾作塵”的滿目瘡痍;而積極面對,則將感受到“化作春泥更護花”的美好重生。
其實,這世間,本就沒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態。
顯然,歷經世事的許老先生深諳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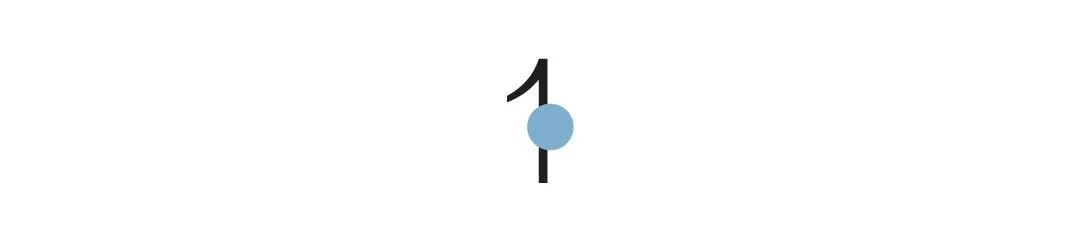
沒有哪段人生不曲折
沒有誰的生活不煩惱
1930年7月,江蘇無錫的許氏望族迎來了一對雙胞胎男孩兒。
孿生弟弟身體健全,而作為哥哥的許倬云由于先天肌肉萎縮導致手腳彎曲,雙腳無踝,是個天生殘廢。
在許倬云的記憶中,小時候的自己總是獨坐在家門口,看同齡孩童們歡快嬉戲。
而那份童趣,與自己無關。
待到可以杵拐行走,許倬云依然在家中自修,不能同小伙伴一起去學堂學習。
那一刻,小小年紀的他明白了:
這一切皆因自己是個行動不便的瘸子,是個徹頭徹尾“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
雖然很無奈,但不得不承認,生活就是這樣:從不輕易放過誰。
看不清方向的迷茫,找不到依靠的無助,完不成夢想的遺憾……
種種辛酸,樁樁不易,總在生命旅程中輪番上演。
總之,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劫,你躲不過,也逃不掉。
沒有誰比誰更容易,只看誰比誰更能扛。
想明白這一切,許倬云放下心結,開始將家中書房當學堂,潛心學習。
他研讀古書,從《詩經》《左傳》到“三禮”“四史”……
博覽群書讓他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也為他打開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門。
人生匆匆幾十載,有人勞碌一生,卻只為衣食住行茍且眼前;有人在短暫迷茫之后,用讀書趕走平庸,去遇見更好的自己。

只能說,書,是平凡人的救贖。
機會,總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憑借扎實的知識儲備,許倬云考入臺灣大學,并在讀研第二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績拿到了“李國欽獎學金”赴美留學的資格。
遺憾的是,該獎學金要求獲得者必須身心健全。
而許倬云身體殘疾,自然沒有入圍的資格。
驚聞這個消息,他震驚了。
但為了這個機會,他也努力去爭取過,但收效甚微。
只能說,這一次許倬云真的受傷了。
他沮喪地問:“為什么這種事總發生在我身上?”
待冷靜下來,他又告誡自己:“這世上確有很多事讓人無能為力,很多問題最終結局不盡如人意,那能怎么辦呢?就盡我能力,做我能做的事吧。”
之后,他心平氣和地去上課,去自習……就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過。
眾人欽佩他的泰山崩而不變色,而愛才的臺大校長更是親力親為地替他奔波。
最終,在眾導師的幫助下,許倬云終于得償所愿,重拾赴美留學的資格。
他的人生,開啟了嶄新的篇章。
作家劉震云說過,世上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挑,就是日子不能挑。
在命運的旅途中,沒有哪段人生不曲折,沒有誰的生活不煩惱。
每個人都得負重前行,誰也沒有豁免權。
但無論如何,只要不放棄,陽光總會有照進來的時候。

沒有完美的選擇
全靠權衡與取舍
就這樣,27歲的許倬云去到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
梅花香自苦寒來,5年寒窗,32歲的他順利拿到芝大博士學位。
頭頂著常青藤博士的光環,很多名校向他伸出了留校的橄欖枝,但他都斷然拒絕了。
他一直清楚地知道:
正是因為當年恩師傅斯年的慧眼,自己才得以走上博古通今這條正確的成才之道;也正因母校一眾導師的出手相助,自己才有機會遠赴重洋,學業大成。
如今,是時候該回報師恩了。
因此,許倬云欣然接受臺灣大學的邀請,回臺任職臺大歷史系系主任。
朋友們疑惑他的選擇,紛紛勸他“不要因大失小,丟個西瓜撿粒芝麻”。
他卻說:“我,深知自己天生體殘,若想成事,唯有遵從本心,往里走,安頓好自己,方能達成所愿。”
是啊!有人星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孰是孰非無需評判。
人生,哪條路都不好走。
追求理想需要冒險,選擇安穩需要放棄內心所愛。
但聽從內心的聲音,盡力而為地走好自己選擇的路,便是最好的人生。
之后的幾十年,許倬云將自己的一腔熱血獻給了三尺講臺,獻給了學術研究。

他孜孜不倦地傳道授業,無數的青年在他的諄諄教誨下脫穎而出。
其中,最著名的學生莫過于王小波。
1984年,32歲的王小波注冊在許倬云名下讀研,并在此期間進行《黃金時代》的創作。
眼見因創作進入瓶頸期,苦悶的學生偶爾會流露出放棄的意愿,許倬云緩緩地說:
所謂人生,便是盡一份心力,求一份結果。
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義無反顧地為之努力。只要最終所得是心中所愿,那就是成功。
許倬云的話語令王小波醍醐灌頂。
之后,他在文字上猛下功夫,定稿的作品文字精煉,文風戲謔而浪漫。
最終,《黃金時代》獲得1991年度文學類中篇小說大獎,王小波也因此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多年后,王小波的妻子回憶起那段師徒間亦師亦友的時光,感概萬分:
“許老是小波最為推崇的老師。因為從許老那里,我們學到了:這世上唯一的成功,便是遵從內心的選擇,然后傾力而為去努力。”
沒有完美的選擇,全靠權衡與取舍。
就像余世存在《時間之書》里所說:
“年輕人,你的職責是平整土地,而非焦慮時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而成年人的勇敢,是既然選擇了遠方,就要義無反顧地走下去,直至成功。
這世間,最質樸的行事規則便是:你只管盡心選擇,全力奮斗,其他的交給時間。

總有一個人的出現
會讓你覺得人間值得
電影《玻璃樽》中說:
“我們每個人生下來的時候都只有一半,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世間行走。”
對于愛情,許倬云也有類似的認知:
“這世間,必有這樣一個女孩,能識人于牝牡驪黃之外,能像伯樂識馬般發掘我都另一面,而我也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要知道,身為臺大歷史系主任的許倬云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學術上,無心顧及花前月下,郎情妾意。
而孫曼麗的出現,對他而言,就是“上天賜與的福分,讓自己終于遇到了不在乎牝牡驪黃的伴侶”。
孫曼麗,長相姣好,家境殷實,是許倬云的學生。
縱然身邊有眾多的追隨者,可她獨愛許倬云那股子不服輸的勁兒。
她曾欣喜萬分地對同伴說:
“許老師真的很有才華,也從不因為自己身體不方便就輕易妥協。”
都說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完美,只是因為他獨特。
那種感覺便是:說不出他的好,可任誰也代替不了。
慢慢地,孫曼麗活潑開朗的性格讓許倬云如沐春風;而許倬云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也讓孫曼麗頗為傾心,兩人很快陷入熱戀。
對于深愛的人,婚禮是否隆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身邊的那人,必須是那個心愛的她。
1969年,許倬云為孫曼麗舉行了一個簡潔的婚禮。
婚后,許倬云潛心學術,對生活瑣事絕不插手。
而孫曼麗則從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搖身變成料理家務的一把好手,承擔起家事。
許倬云體弱,孫曼麗就照料他的生活,為他布置了一個溫馨恬靜的家。

即便后來,許倬云的身體狀況不可控地惡化,只能右手食指活動,寫作只能口述。
此時,孫曼麗便是他的工作助理:為他翻譯原著,查詢資料,替他的著作取名。
對此,許倬云萬分感概地說:“她是我一輩子的福氣。如果有來世,我還盼重續今生之緣,但是該由我照顧她了。”
兩人琴瑟和鳴,攜手共渡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
是的,行走在人世間,無論你身處怎樣的狀態,總有一人懂你心酸、疼你入骨;也總有一人能在雨天替你撐傘,給你安慰。
某乎上有個提問是:在哪個瞬間你感受到了世界的溫柔?
其中一條高贊回答是這樣的:
世間眾多薄涼,但總會有一個人,他的出現會趕走你生活中所有寒意,給你一個溫暖的人生;讓你無悔最初的選擇,真心感嘆“這世界,有你就好”。
余生很短,但要堅信,總會有人讓你覺得人間值得。

命運從不公平,總能輕飄飄奪人幸福,又惡狠狠播撒苦難。
但命運也很公平,苦盡自會甘來,絕處終將逢生。
縱觀許倬云的人生,命運只是殘缺了他的身體,卻健全了他的人格。
因此,他在《往里走,安頓自己》書中,告訴世人:
“面對苦難,面對迷茫,你是什么樣的人,就有什么樣的人生。艱難時沉住氣,默默蓄能,總能熬出人生的甜。”
漫漫人生路,遭遇的不同磨難,陷入的不同困境,本是生活的常態。
正如巴爾扎克所說:
“人生并非充滿了玫瑰花,倒是前行路上荊棘遍布。”
而真正的勇者,就是在看透這生活的本質后,依然義無反顧地擁抱生活、勇往直前。
那些殺不死你的,終將使你更強大。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