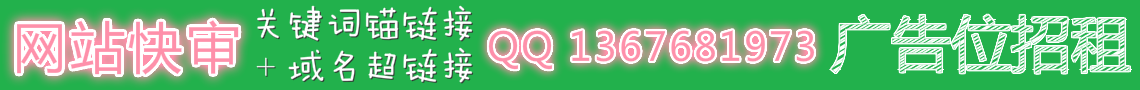在文學體系當中,“底層”指的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地位上處于社會最下層的民眾,他們是整個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最需要社會去給予關心和關注的弱勢群體。
在這些人群當中,主要是以進城務工的打工者、下崗工人和依然在貧瘠農村勞作的農民為主,他們為溫飽問題掙扎在生活的最底層,夜以繼日的生存在被遮蔽的工廠和狹小的出租屋內,終日為生活到處奔走,無暇顧及個人情感的走向。
實現了對生命價值的真實觀照,使電影具有了新的人文意義。

關注弱勢群體
弱勢群體是被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排除在外的群體,他們常常遠離話語權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轉型產物。所謂“弱勢”一般具有三個含義:一、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常處于很困難的狀況之中,無法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二、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這是由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共同造成的,比如制度、政策的原因,智力、性別的原因;三、在政治和話語權力層面,能夠掌握的資源很少導致他們很難發聲。
依照這三個含義來對第六代電影中的人物進行對照,會發現其電影中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弱勢群體:農民工、下崗工人、邊緣青年、小偷、妓女等。第六代導演通過對底層弱勢群體的塑造不僅豐富了電影銀幕上的弱勢群體人物形象,還以審美的方式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面臨著種種嚴峻的問題:經濟結構的迅速調整造成的部分社會民眾的失業,市場化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追求經濟效益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社會階級化、貧富兩極化、社會群體弱勢化的現象日漸凸顯。
而此時的電影界,“第五代”導演沉溺在歷史鏡像中進行反思,主旋律電影在改革大潮中歌頌時代巨變,商業電影在市場經濟中打造娛樂空間,而“第六代”導演將帶著真誠和關懷的目光投向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以鏡頭去呼吁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張元導演從《媽媽》到《過年回家》,殘疾人、精神病患等社會弱勢群體就一直張元鏡頭下頻繁出現的人物主體,著重記錄他們的生存狀態以及社會轉型期給他們帶來的困惑。正如他在采訪中所說到的:“我是一個邊緣狀態的藝術家,所以對邊緣人有很深的思考。”
張元的另一部電影《兒子》因為對社會群體的真誠關懷在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榮獲金虎獎,國際影壇對他的評語是:“獎勵其徹底的真實,獎勵其對人物和觀眾的尊重,獎勵其對中國電影的獨特貢獻。”

賈樟柯導演從電影事業的開始就沒有放棄過任何一個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機會,他的影片《任逍遙》包含了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弱勢群體:城市邊緣青年、下崗工人、底層民工、邊緣藝人等,將城市中的邊緣青年塑造成電影的主角在以往傳統的電影中都不曾出現,賈樟柯卻給予他們講話的權利,關注他們的情感與理想,解讀他們的內心世界,體現了賈樟柯所追求的電影理想。
除此之外,還有王小帥對農民工生存境遇的關注,何建軍、婁燁對同性戀情感的關注,路學長、王超對城市底層民眾的關注,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弱勢群體的精神關照,他們用電影去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去捕捉時代變遷中最真實的感情,表現了他們對底層生命的尊重和關愛。

尊重個體情感
尊重社會中個體的情感自由是第六代導演電影作品中時刻關注的內容之一。在“第六代”導演的視野中,每一個行走著的生命個體都是他們想要記錄的內容,每一個個體的情感走向都值得他們去關照,這彰顯的是“第六代”導演對底層群體的尊重與憐憫。
電影《小武》中的梁小武是賈樟柯電影中非常經典的一個角色,盡管他是個小偷,但是他與許許多多生活在底層的民眾一樣,都渴望得到浪漫的愛情,純真的友情以及父母對他的關愛。
導演將視角聚焦于小武身上,將小武的情感經歷真實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讓觀眾和小武一起經歷了情感的變化,這體現了賈樟柯對生活在底層的邊緣人群情感的尊重。張元導演的回歸體制之作《過年回家》中主人公陶蘭因過失殺了繼父的女兒于小琴,在監獄中度過十七年的陶蘭即將面臨出獄,卻處于是否回家的矛盾心理中。

陶蘭作為社會邊緣人,她內心的情感在經過十七年的牢獄之災之后變得異常的敏感,一方面她渴求與父母見面受到親情的關懷,另一方面她又囿于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
在電影中,張元以陶蘭的個人情感為出發點,在書寫她生活遭遇的同時也挖掘了她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張揚的電影《愛情麻辣燙》盡管是迎合市場的電影作品,但是其深處仍然充滿著對社會民眾的關懷。
在這部電影中張元直接以社會個體的情感生活作為切入點,用分段式的敘事結構講述了不同人群的情感遭遇和在當下社會環境所遇到的情感問題,電影刻意規避了深層次的思考和具有使命感的說教,以輕松的節奏將現代人的情感問題展現給觀眾,充滿了人間溫暖。

《東宮,西宮》是中國大陸第一部直面同性戀問題題材的電影,電影將同性戀群體在社會中遭受的問題直接展現在觀眾眼前。在傳統的主流價值觀中,同性戀群體常常被冠以“變態”、“邪惡”的詞語,他們的情感問題是主流社會一直羞于啟齒的并且常常逃脫不了被歧視的命運。但在張元的《東宮,西宮》中,導演賦予了阿蘭說話的權利,讓同性戀者講述自己的情感遭遇。
在其講述的過程中,觀眾也融入到了講述著情感體驗當中,很容易得到觀眾的理解與共鳴。影片整體上展現了同性戀群體的被擠壓的生存空間和文化空間,再現了同性戀群體壓抑孤獨的情感狀態,體現了導演對于每一個個體的情感的尊重。

“第六代”導演的電影當中大部分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體的事件構成,這些個體都是一個個底層如泥土般的生命,他們可能是為了生活而四處輾轉的民工,可能對前途迷茫而四處游逛的邊緣人,可能是在都市找不到身份歸屬的農民……盡管他們有著不一樣的生活經歷,不一樣的情感遭遇,不一樣的價值訴求,但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值得被尊重的生命個體。
展現人性傷痛
“第六代”導演本身的成長和生活體會導致了他們一直極力關注底層群眾的殘酷人生和傷痛體驗。底層民眾大多生活在社會的轉型期,他們一方面經歷國家體制變革帶來的陣痛,另一方面又因自身渺小趕不上時代步伐而焦慮,在現代化工業化面前他們苦苦掙扎,卻又無濟于事。

電影《站臺》中的文工團就是時代發展的產物,面對經濟體制變更帶給他們的創傷,他們只好四處奔波走穴,但個人的努力仍然趕不上時代的變化,他們每個人的奮力掙扎最終還是如夢幻泡影,逝去的時代和美好的青春帶來的只有傷痛。在電影《三峽好人》中,生活給底層勞動者帶來的只有苦悶,他們辛苦工作換來的卻是流離失所。
這在現實中對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赤裸裸的傷痛,并且這種因時代變遷而帶來的傷痛是很難痊愈的。除此之外,在“第六代”電影中造成底層人們傷痛的還有理想的幻滅,賈樟柯在他的隨筆中談到底層的群眾每個人放棄理想都有非常具體的原因,每個人都要承擔對生命的責任,對別人的責任。

就像顧長衛電影《立春》中王彩玲,她就像每一個平凡生活中不甘平庸在追夢道路上的你我,她是每一個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的人的縮影,盡管她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但是在現實面前她仍有承擔理想幻滅所帶來的傷痛。
“第六代”導演在電影中展現人性傷痛時會呈現出一種強大的悲劇力量,使得影像在呈現底層民眾生存境遇時充滿強大的震撼力。《任逍遙》中斌斌與小濟對前途與理想充滿了想像,但依舊無法逃脫時代帶給他們的悲劇命運;《兒子》中母子兩人拼盡全力也無法治愈父親的精神問題;《安陽嬰兒》中妓女馮艷麗無法擺脫的賣淫之路;《十七歲單車》中務工青年郭連貴最后也沒有找回自己的身份象征——自行車……

“第六代”導演在對社會弱勢群體施以關懷的同時并沒有給他們一個所謂的圓滿的結局,或者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給他們的電影蒙了一層神秘的悲劇色彩,但卻是對社會底層民眾生活困苦的真誠披露。
“第六代”導演試圖關注并思考時代變化的巨大洪流中的人的生存狀態,展現時代巨變和理想失落帶給底層民眾的人性傷痛,這正是“第六代”導演審美價值的有力彰顯。“第六代”導演試圖用鏡頭語言書寫著邊緣個體的生活遭遇,這不僅是對電影獨特藝術形式的探索,更是對傳統審美價值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