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昆汀的個人風格沒有借鑒馬丁·斯科塞斯。
很難說,王家衛《旺角卡門》的劇本結構沒有參考《窮街陋巷》,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的敘事方式沒有致敬《窮街陋巷》。

《窮街陋巷》是馬丁·斯科塞斯和德·尼羅的第一次合作,自此開啟了兩人長達近50年并至今還在延續的合作關系。
這對黃金拍檔是電影史的幸事,更是觀眾的福音,為我們奉獻一部部精品的同時也讓德·尼羅成了斯科塞斯的電影符號之一。

除他之外,《窮街陋巷》也是馬丁個人風格形成的序章。
密集的臺詞,配樂敘事,豐富的鏡頭語言,多變的場面調度,神乎其神的剪輯,對社會的審視,以及意大利情結,這些都成了他日后電影的必備元素。

在《窮街陋巷》里有兩處可見馬丁對視聽語言的精準掌控。
一處是主角查理醉酒,鏡頭隨著角色身體的擺動同步晃動,給人以暈眩的觀感,那種意識不清、身形飄忽的感覺特別強烈。
其實,馬丁為了達到這種鏡頭語言,專門把攝影機綁在男主的身上,這樣一來,攝影機成了電影的一部分,而不是冷冰冰地記錄。
讓其參與敘事,讓其代表人物傳達情緒,導演的意圖會表現得更直觀,觀眾也可以從中很快體會到導演的用意,一舉兩得。

另一處是片中大量的手持攝影。
盡管當年馬丁這樣做是為了節省經費,但這種沒錢而來的辦法恰恰讓影片的主題得以展現。
鏡頭不停地晃動表明角色內心的迷茫與躁動不安,他們處在無序、混亂的社會之中,不知未來在何方,也不知自己該去干什么,終日無所事事,渾渾噩噩的度日。

偶爾會擔心生活耍了自己,可一時的振奮大多時候都是三分鐘熱度,酒醒后又是明日復明日。
這就是當時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現狀,活一天算一天,對什么都提不起興趣,德·尼羅飾演的強尼便是如此。

這種寫實也是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風格之一。
他的電影沒有那么多浪漫主義,有的是引發思考的現實主義。
斯科塞斯電影中的主角基本都是孤獨的、反社會的,而馬丁通過解構他們的行為與心理發現活著的意義。

馬丁尊重角色的個性與自由,但他并不是無休止的放縱,任由角色打破規則、天馬行空,而是讓觀眾看到他們的行徑后明白人怎么才能活得有意義。
人來到這個世界本身是無意義的,但是人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讓自己變得有意義,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即使平凡,也是好好活,也是有意義的事。

在《窮街陋巷》中,強尼從始至終都不懂自己存在的意義,他沒有信奉的主義,自然不懂為什么而活著。
他的依托就是得過且過,今天跟朋友A借錢,明天跟朋友B賒賬,后天用朋友C的錢補朋友D的窟窿,與擺爛無異。
他充滿消極頹廢、悲觀失望情緒,深感自己苦悶、孤獨、被遺棄,因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蕩不羈,標榜個人的生活、自由便成了他掩耳盜鈴的把戲。

好友查理并不想強尼就此墮落下去,他幾次三番拉強尼回歸正途,可他自己不爭氣,還用狂妄自大掩蓋自己窩囊頹廢的本質。
重情重義的查理也因強尼難以正常生活,他的叔叔想讓他繼承自己的飯店,但條件就是與強尼斷絕來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叔叔看得很透徹。

但查理的內心并不堅定,如同他輕易動搖的信仰一樣。
不知及時止損,果斷割舍,只知哥們兒義氣,到頭來誰也救不了,還搭上了自己的前途,沒有將強尼重新塑造,更沒有成就自己。


強尼的價值觀是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查理則是生命是強烈的,上帝是可信的。
但馬丁·斯科塞斯否定了他們的價值觀,借助影片結尾查理和強尼紛紛受傷且無助呻吟來告訴觀眾,真正的存在主義不是強調個性和自由,而是懂得選擇。

《窮街陋巷》有的不止是哲學思想,還有對新好萊塢時代即將來臨的推進。
馬丁·斯科塞斯以《窮街陋巷》打響名頭,跟科波拉、斯皮爾伯格、盧卡斯等電影小子一起革新著傳統好萊塢。

以前的好萊塢電影注重戲劇沖突、完整結構,大團圓結局,臉譜化角色以及連續性剪輯。
在《窮街陋巷》中幾乎很難看到這類特質,意識流敘事和跳切剪輯,開放式結局與難辨好壞角色,《窮街陋巷》跟傳統好萊塢大相徑庭。
對于馬丁來說,《窮街陋巷》是雛形,有些地方不盡如人意,三年后的《出租車司機》才是完全體,才是他成為新好萊塢四杰之一的階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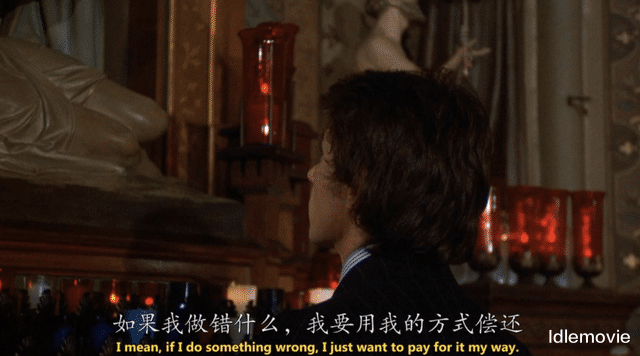
但大師也不是一開始就是是大師。
處女作《誰在敲我的門》發行不利,遠赴歐洲追求電影夢,郁郁不得志后回母校紐約大學任教。
之后為籌備拍片資金,接受羅杰·科曼的邀請,執導B級片《冷血霹靂火》,盡管票房大賣,但被導師譴責忘記初心,順應好萊塢主流。
馬丁回到《窮街陋巷》劇組,繼續拍攝自己鐘愛的作者電影,終用個人第三部電影為自己打了一個翻身仗,一代大師由此走上封神之路。

可惜現在的電影圈已經很難再有大師出現了,再加上戈達爾的剛剛離世,在世的大師更是屈指可數了。
畢竟頻繁地翻拍、續集、超英,全世界集體向右的思潮,改革和創新顯得格格不入,電影的春天會有一個極其漫長的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