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明星考編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易烊千璽、羅一舟、胡先煦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國家話劇院的擬聘名單當中。
考核流程是否合規,遭到質疑。
對此,國家話劇院回應:尚處公示階段,并非已錄取。

但依然無法平息爭議。
而隨著輿論發酵,一家媒體也攤上事了。
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把普通人針對明星考編提出的合理質疑表述為「煞有介事」。
并將這場爭議歸結為大眾對娛樂圈的不滿情緒,以及「小鎮做題家」的被剝奪感。
字里行間流露出嘲諷的味道。


引發爭議的文章節選
頓時激起了許多網友的憤慨。
畢竟,「小鎮做題家」本意是自嘲。
這個詞出自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
原本指的是出身小鎮的學生,通過努力刷題考上高校,畢業后卻發現處處受挫,自己只會做題。

它是一種消解無奈情緒、抱團取暖的出口,能夠激起許多普通人的共鳴。
沒成想,曾經的「自嘲」,如今成了「被嘲」。
而真正的諷刺對象,卻被遮蔽了。
「小鎮做題家」的苦澀,又何嘗得到過正視?

對于很多人來說,做題是唯一的出路。
就如同如今爆火的董宇輝。
他生活在陜西農村,家境一般。
也曾自卑過,把自己形容得非常難堪。
「出身農村,身材矮小,頭又大又丑。」

他沒有拿到一手好牌,只能努力學習,期待改變命運。
正如他曾激勵許多高考學子的金句那樣。
「當你背單詞時,阿拉斯加的虎鯨正躍出水面;當你算數學時,南太平洋的海鷗正掠過海岸;當你晚自習時,地球的極圈正五彩斑斕。」
直到高三那年,他終于成功逆襲,將分數從320分提升到了600分左右,考進了西安外國語大學。
之后,又進入新東方,得以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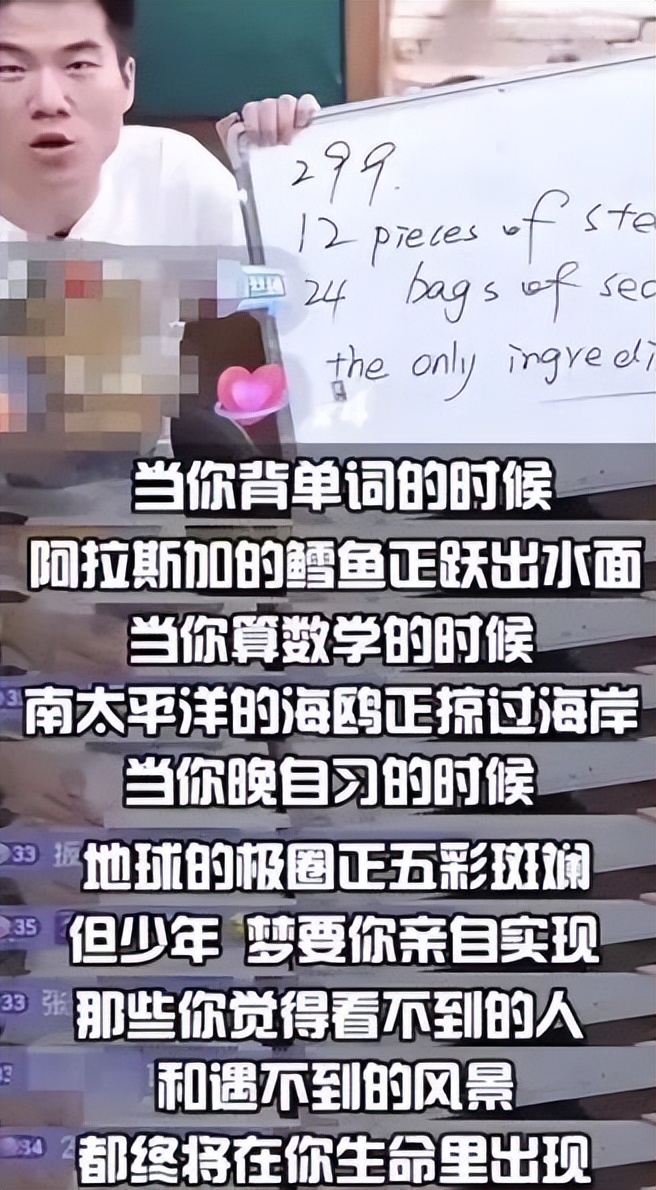
高考,成為了他人生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男性如此,女性更是如此。
我們見過太多重男輕女的家庭悲劇。
紀錄片《出·路》中的馬百娟,出生在甘肅的一個貧困縣。
她有自己的夢想,想去北京上大學,然后打工,每月掙1000塊錢。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她渾身都有勁兒,眼里始終閃著光。
在走三十里的上學路時,她全程都笑著走完。

在課外時間,她沒辦法讀書。
還要幫家里一起收谷子、做飯、做家務……
但一有時間就捧著書讀。

最終,她卻早早輟學,16歲就結婚生子。
這不是因為她學習成績不好,主動放棄,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在接受采訪時,馬百娟之后的人生安排就被父親非常直白地指了出來——
「靠女婿。」

這種被安排的命運是許多大山女孩們的縮影。
而對于她們來說,高考是能夠擺脫困境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張桂梅的華坪女高就是為此建立的。
讓許多讀不了書的「馬百娟」們可以擺脫自己的命運。

也因此,設置了嚴苛的制度。
每天早晨5點起床跑操,零點才能睡覺,吃飯時間只有10分鐘……
讓學生們每天都泡在題海里。
不可否認,這種應試教育確實有壞處,消磨了人的個性。
但就如張桂梅所說。
「人家說做題對孩子不好。我們沒辦法,我們只有這個辦法。」
這是不得不做的犧牲。

高考就像一個可以突破階級的小窗,藏著普通人最質樸的愿望。
考個好大學,找個體面的工作,有一個比現在要好的未來。
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許多人都孤注一擲。
在紀錄片《高考》中展示的陪讀家庭就是如此。
有的家長放棄自己經營已久的事業陪讀。
有的咬牙借錢陪讀。
甚至還有的「因教返貧」。
但與付出巨大代價相比的是,殘酷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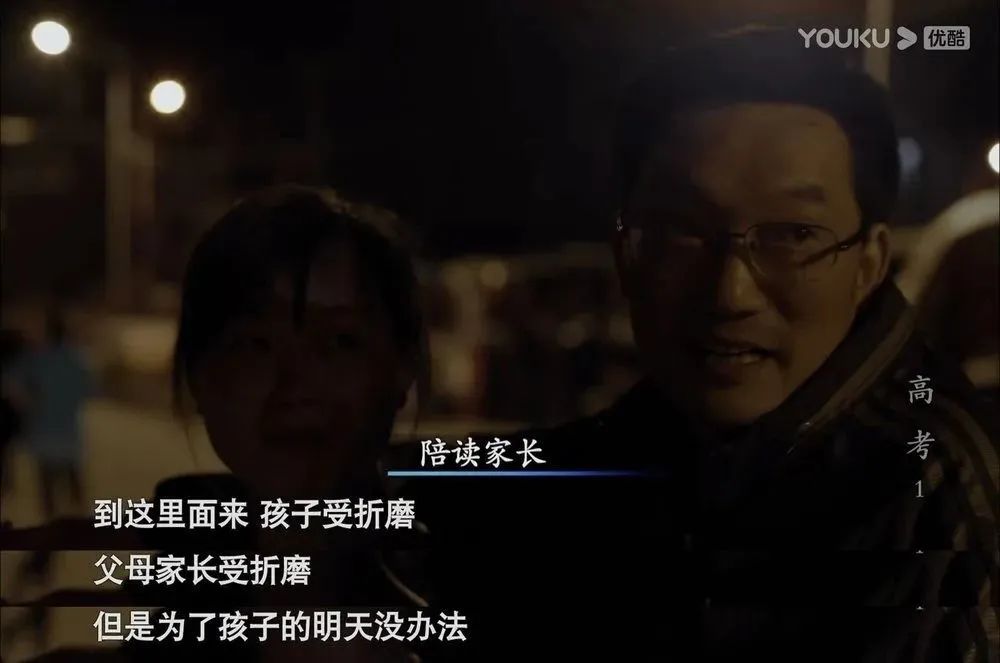

走出小鎮后,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滿意的結果。
階級的差異始終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紀錄片《出·路》就撕開了這其中殘忍的真相。
它跟蹤了來自農村、小鎮、城市三個地方的孩子,展示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來自農村的馬百娟就如前文中所說的那樣,始終沒有擺脫自己的命運,眼神也沒有了之前的精氣神。

而來自城市的袁晗寒的情況卻大不一樣。
她的家境很好,有很多能夠試錯的機會,可以心無旁騖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17歲時,因為學業壓力太大,在家人的支持下,她選擇休學。
之后,就宅在家里畫畫、看書、看電影……

在她眼里,旁人邁不過去的坎兒,都不是大事。
一次,她突然靈光一閃,又拿著家里的錢開了一家咖啡館。
即便沒多久就關了門,她也沒有感到多少心理壓力。
因為之前就和媽媽就達成了共識。
「如果失敗了就當交學費了。」

之后,袁晗寒又跑到國外上大學,周游歐洲。
還在北京注冊了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
她的人生恣意昂揚,從不需要為未來操心。
就如同導演在采訪中所說的,她對付的不是現實,而是「無聊這個敵人」。

來自小鎮的徐佳則是許多「小鎮做題家」的縮影,拼命抓住高考的機會。
不斷沖刺、修正、涂抹、重置,付出巨大的代價。

徐佳也曾告訴自己考不考得上都無所謂。
但這只是一種心理安慰。
他還是在意那個結果。
因此,選擇復讀兩年,心理壓力也非常大。
有一段時間,他開始渾身冒汗,手抖。

所幸,最后一切沒有落空,上了一個還算滿意的大學。
但這不算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等到畢業,開始找工作的時候,他又不得不面臨生存的挑戰。
在網上海投,奔走在去面試的路上,但只收到了很少的offer。

后來,好不容易跟一家公司簽了約。
但徐佳也并不高興,對未來的發展情景,公司待遇一片迷茫。
形容自己好像是被賣出去了。
徐佳沒有因為一個好的大學就走上人生的高速通道,也不能像袁晗寒一樣擁有追逐夢想的舒適圈。
從小鎮走出來后,他依然渺小卑微。
對于他來說,那些金句雞湯描繪的美景還是那么難以企及。

這也正如《東京貴族女子》里,從小鎮出來到大城市打拼的美紀。
四處碰壁,看不到任何希望。
甚至為了湊夠學費,成為夜總會的女公關。
普通人要在大城市扎根的過程艱難無比。
「從老家出來,被壓榨剝削,我們就是東京的養料吧。」

在巨大的階級隔閡中,拼命刷題或許也換不來「逆天改命」。
但「小鎮做題家」那段努力的人生不該被他人隨意貶低。
為高考拼搏的歲月,讓普通人擺脫了當時的困境,到達了今天的高度。
依然熠熠閃光。

「小鎮做題家」固然帶著自嘲的無奈。
但這個詞并非代表對自我的否定。
相反,這是人們奮力掙扎,反思應試教育,重新構建自我的一個過程。
在《十三邀》中,教師黃燈提到了近幾年她觀察到的大學生現狀——
身上留有高中時代的刻痕,他們冷漠、憂郁、麻木、害怕犯錯、無所適從。
就好像一個個「空心人」。

而這些大學生需要的是「找到自己」。
「正視自己的生活經驗,直面自己,和真實的生命體驗打通。」
去詰問,我的失落感究竟從何而來?問題出在哪?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鎮做題家」何嘗不是在用諷刺現實的方式揭露現實。
說到底,它的諷刺對象,從來不是那些失意的畢業生。
而是應試教育的深層矛盾,和長久以來的教育不公現象。
人們所期待的,無非是「公平」二字。
這也是為什么,明星考編事件惹了眾怒。
易烊千璽、羅一舟、胡先煦等明星當然可以去考編。
在娛樂圈中,也有不少明星有編制。
孫紅雷、秦海璐、劉燁、段奕宏、胡歌、廖凡、倪大紅等都是國家話劇院的演員。

來源:國家話劇院官網
但關鍵點在于他們以何種方式取得編制。
如果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公平競爭下收獲這份編制的名額,自然不會有什么爭議。
而在這場考編風波中,許多網友都提出了質疑。
比如,易烊千璽、羅一舟、胡先煦三人是否滿足招聘條件。
國家話劇院的招聘公告顯示,該崗位招聘對象是應屆畢業的非在職人員。
但三位明星都早早和經紀公司簽了合同。
這還能算是非在職人員嗎?

但截至目前,國家話劇院并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回應。
反而讓許多普通人不惜放棄工作機會,小心翼翼保護的應屆生身份,一下子變得荒謬了起來。
選拔方式的不透明,不公開才是激起網友憤怒的根源。

同時,考公考編難度高、競爭壓力大,早已成為了大家的共識。
根據國家公務員局發布的公告顯示,今年國考共有212.3萬人通過了資格審查,但實際錄用人數只有3.12萬人。
平均每68人競爭一個崗位。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是一件「不死也要脫層皮」的事情。
許多人要備考一兩年,甚至六年的時間才有幾率考上。

而捫心自問,大家真的喜歡體制內的生活嗎?
不見得。
對很多人來說,這只是充分權衡利弊后的妥協。
在不確定的生活里尋求一份安穩。

可頂流明星不同。
他們本身就有很多選擇權。
而選擇進入體制,不是為了生存,而是機會。
不僅能借機營銷一波「體制內男友」的人設。

還可能獲得一定的資源傾斜。
普通人削尖了腦袋追求的安居樂業,到頭來變成了明星鍍金的工具。
這樣大的落差是許多人心理上無法接受的,所以引來了廣泛的討論。
在這種情況之下,「小鎮做題家」的焦灼也應該被看見。
正像去年那篇火遍全網的中科院博士論文致謝中寫道的:
「人后的苦尚且還能克服,人前的尊嚴卻無比脆弱。」
「身處命運的旋渦,耗盡心力去爭取那些可能本是稀松平常的東西,每次轉折都顯得那么的身不由己。」

總有人抓了一手「爛牌」,但也努力在生活的泥潭中掙扎,向上生長。
所爭取的,不過是一個走出逆境的機會。
所守護的,不過是一份不愿認命的尊嚴。
「小鎮做題家」的苦澀,也正是無數普通人的痛點。
而這,本不該被冷嘲熱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