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期了差不多兩年后,婁燁的新作《蘭心大劇院》上映。
《蘭心大劇院》未必算婁燁作品里的上乘之作,但絕對夠有爭議。有人指責這是婁燁近年來最大的滑鐵盧,有人說這是屬于婁燁的一次自我突破。
影片有兩個提供改編靈感的原著小說:虹影的《上海之死》和橫光利一的《上海》。
前者提供了影片中關于諜戰的部分,后者則以戲中戲的形式融入進來,以此完成影片在情感與人物關系上的互文。

《蘭心大劇院》講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太平洋戰爭前夕的一段諜戰故事:著名演員于堇返回上海。表面上,她回來是為了幫助舊愛譚吶完成《禮拜六小說》的排演,但這背后,她的歸來似乎又有著更多、更復雜的目的:營救自己的前夫?為盟軍搜集情報?替養父工作?和愛人一起逃離戰爭?無人知曉她的真實使命。

但她的歸來,已經注定了這座孤島即將面臨的風云變幻。這部電影的文本很復雜,虛實交織、戲劇與現實的邊界被反復打破,要理解它并不容易,所以我們暫時從影片里那些很婁燁、很風格化的東西切入。

手持攝影、長鏡頭、即興表演、黑白影像……這些外在的因素依舊很婁燁。僅從風格上來說,婁燁這次的黑白色調設計和明顯減緩了晃動程度的手持攝影鏡頭都讓《蘭心大劇院》的直接觀感做到了最好。在影院里能看到如此久違的充滿電影感、每一幀都精細雕琢的影像,是幾乎要使人感動落淚的。那種觀影感受酣暢淋漓、純粹而又震撼。情欲上述這些影像風格都還不是婁燁如此迷人的根本原因。婁燁依靠特殊的影像要表達的東西,從來都是小人物在極端環境中的情與欲。從《蘇州河》開始,情欲就一直是婁燁電影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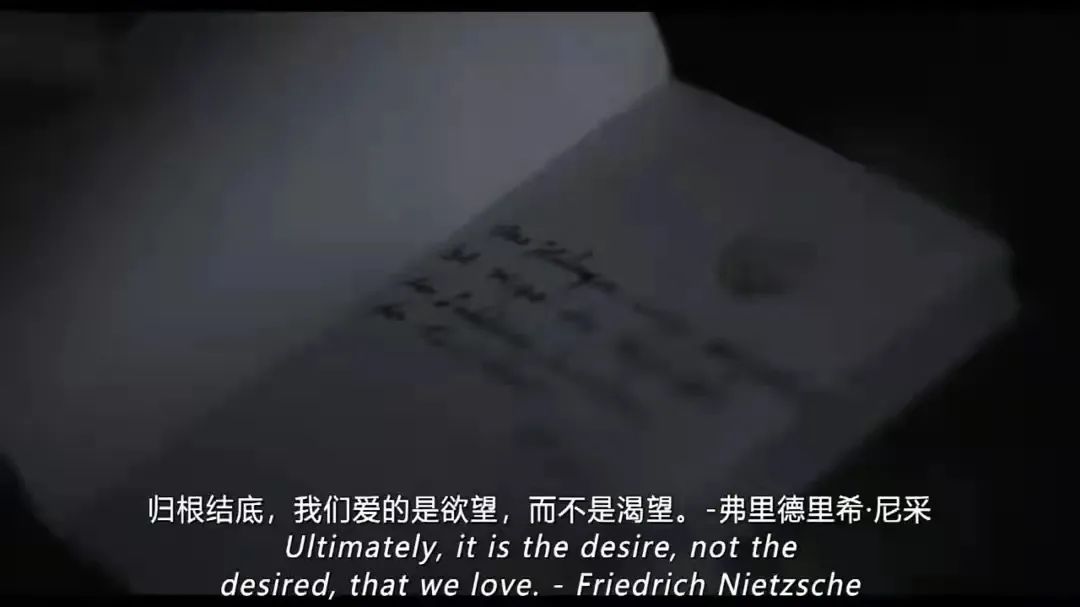
時代變遷中命運多舛、身不由己的個體生命是第六代導演很重要的一個共同母題。但在賈樟柯或王小帥那里,這種命運的無助感來源于時代變遷的歷史車輪直接強加給個人的、無從抗爭的威壓。婁燁影片中的小人物,則從來都是因為有無法割舍的情與欲、有著想要再與命運抗爭一下的不甘才最終被動卷入時代的風云旋渦不得自拔。于堇就是因為有太多剪不斷、理還亂的往日情欲,才重返上海的。她有太多的訴求和使命,每一種使命都對標著一段情感:對譚吶的、對前夫倪則仁的、對養父休伯特的、也有對新認識的女孩子白玫的。岔開去談一句鞏俐老師的表演,不得不說婁燁這次選角很準。在眾多經典角色的光環加持之下,鞏俐如今演戲有了一種很獨特的魅力。她幾乎只要出現在銀幕上,就會自動成為欲望的代名詞。無論她和誰演對手戲,趙又廷也好、小田切讓也好,觀眾都會不自覺地從鞏皇那張高級臉上解讀出情欲感來。

這也是為什么影片里鞏俐催眠小田切讓的那場誘供戲能成立,小田切讓飾演的古谷三郎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美代子已經去世,他只是單純無法抵擋于堇身上散發的情欲。原著里,古谷三郎見到于堇的第一眼就迷上了這個女人。影片里有一段戲,是白玫和于堇的親密戲。兩個女人脫得只剩睡衣,在昏暗的房間里近距離的呢喃愛撫。

下一個鏡頭,于堇已經坐到了窗前,衣衫凌亂、單薄。觀眾無從將兩人之間的關系完全落實到百合向的激情戲上,一切都只停留到情欲的層面。這場戲里的兩個人,于堇和白玫,都展現出了全片中難得的真實自我。兩人之間具體產生了什么情愫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玫和于堇都意識到了這一夜,她們可以短暫的卸下心理上的防線。兩個人都是熱愛表演的女性、同時也都是間諜、是亂世孤島中身不由己的個體、是哪怕身不由己卻依然對藝術擁有信仰的人。

作為重慶軍統方面的間諜,白玫來到上海的任務,就是接近于堇。兩個人離得原來越近,就好像在鏡子里看到了自己。所以,白玫和于堇之間的情欲起源于自戀,看著另一個人的時候,也是在悲嘆憐惜自己的時候。

自戀,幾乎是白玫和于堇在亂世中可以投注的唯一情感。周圍的人都難以依賴,所以只有不斷地望向自己,以此來獲得活下去的動力。所以,也就是在這場情欲戲之后,白玫從于堇身上獲得了于堇曾經的那份執著與癡迷,她最后選擇了舞臺,選擇為了純粹的藝術而犧牲一切,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婁燁自己的內心寫照。

但這樣一個幾乎可以被抽象化為藝術代名詞的符號化人物,卻在戲外遭到王傳君飾演的莫之因的擺弄,最終被莫之因開槍殺死。代表藝術和美麗的白玫被代表資本與權力的制片人莫之因強奸。這里頭的隱喻真的只能點破到這一層了。我們把目光再拉回白玫與于堇的情欲戲之前。在這之前,于堇帶著白玫進入劇院。白玫坐在劇院的觀眾席上看著于堇排練、表演。

于是,劇場空間里有了一個隱在暗處、時刻以第三視角觀察著于堇演戲的視角。這個視角,如果大家懂一點電影理論的話,會很自然地明白它就是攝影機所代表的視角。關于婁燁為什么要在他的大部分電影里運用手持鏡頭,一直都是一個困擾觀眾的迷思。這種鏡頭非常地搖晃、影像極其粗糙。以至于最終它只剩下了一個優點,那就是攝影機所代表的視角的真實性。要想在影片里以如此強調攝影機存在的方式設置一個跟拍的手持鏡頭,導演首先就必須回答這個鏡頭代表著誰的視角的問題。他既然不是代表宏觀視角的上帝,就必須是一個有在場理由的旁觀者視角。

婁燁不是第一次運用這種旁觀者視角的手法。在《蘇州河》里,那個攝影師“我”就一直是這樣一個只存在在鏡頭背后,未見其人只聞其聲的角色,其后續電影中的手持鏡頭幾乎都可以理解為是觀察者角色的變體。在《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觀察者可以被理解為周圍的平民,冷峻地看著姜紫成等人的荒誕故事。在《推拿》中,觀察者則是按摩店的客人,替代著按摩師傅們看著他們看不到的世界。

與眾不同的是,《蘭心大劇院》中的觀察者既是白玫,也是于堇自己。那個不斷跟隨著于堇四處跑動的幽靈不太好被代入為某個具體的角色,其他演員?另一個間諜?圍觀的記者?都不太合理。它只能是于堇自己。白玫望向于堇的目光,是于堇抽離出肉體觀察自我的種種目光中的一個變體。把這事兒說得不那么玄乎的話,就是作為一個演員的于堇,在不斷地以旁觀視角審視自己的表演。這種抽離和旁觀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于堇在多重身份扮演中,預感到了自我即將被吞沒的危險。扮演扮演,是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關鍵詞。《蘭心大劇院》講的是圍繞上世紀上海蘭心大劇院而發生的故事。但影片中的“戲劇表演”卻從未僅僅局限于劇院之內。孤島時期的上海,看似風平浪靜,但四周早已是戰火連天。每個身處孤島的人,都是在假裝扮演著繁華盛世、歌舞升平的假象。

所以,于堇的演出,從她抵達上海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了。她要演戲劇《禮拜六小說》里的女主角秋蘭、要演這出戲的導演譚吶的舊愛、要演拯救自己的前夫倪則仁逃離苦海的妻子、要演一個養父的女兒、要演一位日軍軍官的亡妻。

這些紛繁復雜的身份的交際處,才是那個真實的于堇,看不清、猜不透。回到一開始我對婁燁的那個看法。我說《蘭心大劇院》是很有爭議的一部作品,是因為于堇和婁燁作品里此前的主角們都不太一樣。牡丹、小馬、陸潔、余虹都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時代洪流的人,他們身上充滿著被動選擇帶來的無奈。而于堇,選擇了主動回到孤島,主動選擇再度登臺表演,扮演一個挽狂瀾于既倒的英雄。

一個努力要扮演英雄的小人物,注定要走向悲劇。這場悲劇首先呈現出來的是一種不真實感,虛實交織、夢幻迷離,假作真時真亦假。婁燁從一開始就在形式上暗示了影片的主題:舞臺上的戲劇與現實生活中的諜戰之間的關系被任意打破,上一秒還是血雨腥風的戰斗,下一秒就回到了舞臺上。以至于觀眾對劇情失去了判斷力,很難分清楚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構。解讀《蘭心大劇院》的文本結構因此也就變得不再重要,一來是線頭太亂,理不清楚,二來是現實和戲劇本就是一體的。

被隱去的只有真相,只有悲劇性的結局。擋住真相的,則是人們的情欲。于堇終于到了連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角色扮演的瘋癲地步,所以她需要有一雙眼睛從旁反身觀察自己:我真的是英雄嗎?我真的是我自己嗎?影片高潮的槍戰戲,把這種矛盾糾葛推到了頂點。這段槍戰戲的第一直觀感受就是不真實,好像有人特意排演了一出動作舞臺戲,隱去了某些現實中的真相。在呈現于舞臺上的那個故事版本中,于堇是一個武力值比詹姆斯·邦德都厲害的超級特工。《真·于堇:無暇赴死》。

槍戰沒開始多久,觀眾就以為于堇要因為中彈倒下了。但她居然能一直如戰神一般繼續站起來消滅敵人:那些躲在黑暗中的,突然降臨的敵人。無論對手和于堇進行怎樣激烈的正面對狙,于堇都能奇跡般地躲避子彈,殺死對方。這未免太魔幻了,不太像是真實發生的事情。這段關于諜戰英雄的情節,更像是一個小人物對成為英雄之后的顱內遐想。真正真實的部分則在于,于堇前往酒坊尋找譚吶,兩人被等候已久的日本人包圍,眼看著失去了所有逃脫的可能。

影片最后的一場戲中,譚吶和于堇攤到在酒坊的椅子上,鏡頭一轉,又回到舞臺,仿佛兩人并沒有被殺。但在這之前,還有一場含蓄透露真相的戲,日本人圍住譚吶和于堇后,鏡頭切換到窗外,王傳君飾演的莫之因倉皇逃命,背后則隱約傳來兩聲槍響。顯然第二個開槍的結局才是合情合理的真實情況,于堇和譚吶最終被日本人槍殺。但整部影片自始至終的態度都是在回避這種悲劇性的結局,逃避它,抹除它,讓另一層半真半假的英雄敘事留在臺面上。想要成為英雄,但最終卻難逃普通人命運,為情欲所困,為世俗所困的個體,才是屬于婁燁電影的主題表達。人生如棋,但大部分人最終面度的依舊是無法擺脫成為棋子的命運。已經鼓起莫大的勇氣想要改變命運,最終卻依舊一場空的悲劇,要比被動被卷入來得更殘酷。

說到底,婁燁和賈樟柯一樣,是個骨子里相信,命里也最適合做平民敘事的導演。婁燁電影里所有驚艷世人的角色,都是因為世界被迫將之卷入困局后,轉身若飛蛾撲火般的訣別:寧肯選擇理想與本真,也絕不選擇妥協。所以,這次,那個手持鏡頭后的觀察者才變得那般無可歸納,它是于堇/鞏俐/婁燁共同的自我幽靈,在短暫的抽離中痛苦地逃避著終將要面對的悲劇,在宏大的歷史敘事吞沒個體的低鳴前勉強維持著成為一個英雄的自我意識。-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