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偽紀錄片(mockumentary)是一種與觀眾過招的影像游戲。它讓影像不再只是提供觀眾信息的工具,而是讓觀眾反過來解讀影像的弦外之音,營造強烈的互動性。它可能是經過剪輯與后期制作的片段,也可能是拍攝者死亡后遺留的「拾獲影像」。一般來說,后者比前者更能讓觀眾感受到沉浸式的體驗,仿佛拍攝者在現場與我們對話,并以一種聽天由命的視角,見識悲劇或災難發生的始末。

從主題來看,柯孟融回歸恐怖片領域的新作《咒》比較接近「拾獲影像」的風格。一位焦急的母親李若男突然在網絡上直播,聲稱她與女兒被無形的邪惡力量追殺。六年前,若男的男友帶她前往深山采訪神秘的宗教儀式,卻意外闖進了信徒口中「不能進去的隧道」。她雖然逃出禁地,所有與她相關的人卻都死于非命,迫使她將女兒送往育幼院避難。之后,接受心理治療的若男決定帶著女兒重新出發,但當年的詛咒其實從未消失。若男試圖還原邪教信仰的源頭時,才赫然發現恐怖的真相。

柯孟融的野心不僅是在臺灣的鄉野拍攝一部道地的偽紀錄片,跟同類型作品相比,《咒》電影有個空前絕后的大膽設計,它不只是讓觀眾擔任見證者,還要讓觀眾親身走進劇組精心設計的世界觀,相信片中的異教及祝福咒語確有其事。就像「不要想粉紅大象」的心理學暗示實驗,《咒》打從宣傳期就開始為電影埋下伏筆,你能告訴自己,若男瀕臨崩潰的慌亂情緒,其實是女主角蔡亙晏的精湛演出,但那陰魂不散的八字真言,早已在不斷的暗示與強化下,成為《咒》片尾暗藏的定時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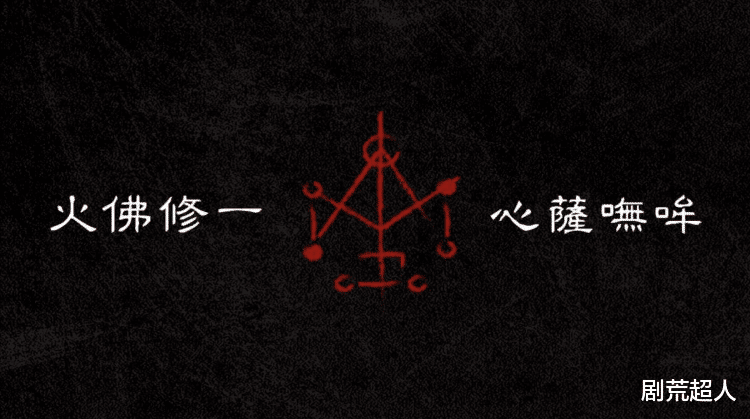
從恐怖效果來說,《咒》的表現已極為出色。片中模仿手持攝影機的鏡頭,其實相當接近肉眼所見的主觀視角,讓觀眾更難回避恐怖直撲眼前的驚嚇。除了預告出現過的攻擊畫面外,若男在家中摸黑尋找怪聲來源的橋段,也成功的喚起我們對暗處的恐懼,將熟悉的生活空間轉化為危機四伏的場所。前述的沉浸式體驗,可說是乘勝追擊的一步好棋,如果它能成功引發里應外合的加乘效果,那么這個似真似假的都市怪談,將會是繼《哭悲》后,對臺灣恐怖片迷的一大挑釁及試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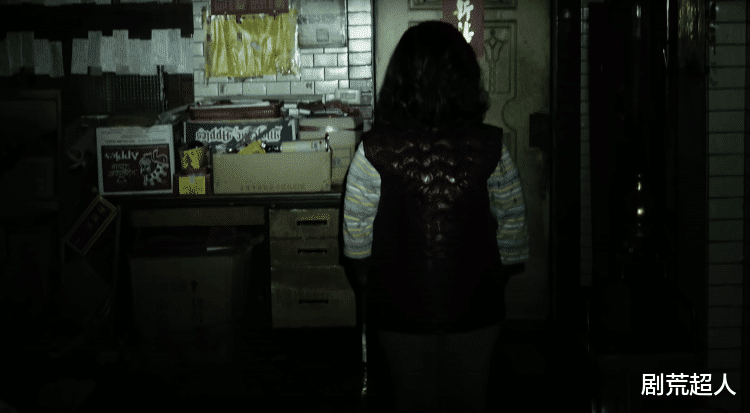
可惜的是,《咒》并未精準踢中那臨門一腳。它雖然順利地將「祝福」與「詛咒」一體兩面的概念植入觀眾內心,卻沒有讓它開花結果。因為它在寫實性與戲劇性敘事上的搖擺不定,一直讓我們難以決定,究竟要將它當成恐怖包裝的溫情電影,還是受盡折磨的母親留下的死前訊息。

然而,如果《咒》無法堅守偽紀錄片冷漠疏離的視角,它苦心經營的劇情機關就無法順暢運作。正所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咒》對血緣及家庭的動人論述,既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致命傷。片中的配樂,在某些緊張的關鍵時刻,反而因為煽情的氣氛,讓觀眾從片中的情境醒來,回到電影院的座位上。

另外,《咒》以倒敘方式將事件分散剪輯的手法,其實有些畫蛇添足。一來,它在觀眾還沒理解前因后果時,就過早披露某些震撼的恐怖鏡頭(例如女主角家人的死亡車禍),此外,它違背偽紀錄片要以假亂真,就必須以線性敘事一氣呵成的基本原則。正因為我們無法用全知全能的視角綜觀事件,命運的殘酷才會更難以預料。《靈媒》及《詛咒》便是如此,片中那些看似缺乏起承轉合的無趣段落,其實就是讓它更加逼真的關鍵。

不過,擬真與否的問題,并未改變《咒》是部優秀恐怖片的事實。它在視覺效果、恐怖氣氛與技術上的成就,可說是一次漂亮的出擊,更洗刷柯孟融先前在《絕命派對》企圖挑戰新類型恐怖片,卻力有未逮的遺憾。而臺灣偽紀錄恐怖片的發展,也就此踏出歷史性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