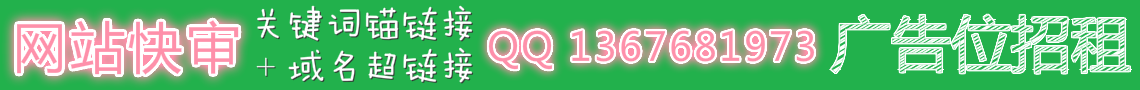廣義地來說,電影空間具有兩方面的定義,其一以觀眾的生活經(jīng)驗(yàn)作為基礎(chǔ),強(qiáng)調(diào)攝像機(jī)的復(fù)制功能,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空間進(jìn)行再現(xiàn);其二則通過蒙太奇手段,對零散空間進(jìn)行拼貼再創(chuàng)造。
也有學(xué)者從多個角度對電影空間進(jìn)行了細(xì)致分類,從文化屬性來看,電影空間可劃分為地理空間、歷史空間、社會空間、精神空間等形式,“狹義的社會空間則是指蘊(yùn)含著某一種特定社會關(guān)系的故事發(fā)生地,它承載著一種社會文化”。

透過四十年代末的電影銀幕空間,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窺見中國民族的歷史記憶,亦能憑借電影的再造空間特性,識別特定年代的都市生活。
而從敘事功能來看,電影又包含情節(jié)性空間,“要求電影中的事件和事件所發(fā)生的空間具有相當(dāng)?shù)年P(guān)聯(lián)度”,即強(qiáng)調(diào)故事情節(jié)在特定空間發(fā)展的必要性,例如家庭環(huán)境空間即為家庭敘事模式的特定空間。

正如中國經(jīng)典電影敘事學(xué)理論書籍《電影敘事學(xué):理論和實(shí)例》里所闡述的那樣,當(dāng)我們在討論電影敘事空間時,也即是在討論空間與故事的關(guān)系及其功能,“闡釋電影敘事中的空間性元素和不同的空間層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電影敘事方式的獨(dú)特個性與特定風(fēng)貌”。
在“偏安一隅的都市之家”中,家庭環(huán)境空間不僅展現(xiàn)著上海摩登家庭的生活旨趣,建構(gòu)著獨(dú)特的文化符號,同時,影片中不同的空間又同時作用于情節(jié)沖突的建立,例如私人家庭空間與公共社會空間、私人空間與摩登家庭環(huán)境的對比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漸構(gòu)建起獨(dú)特的影像意義。
性別劃分家庭、公共空間

在電影《太太萬歲》中,由蔣天流飾演的太太陳思珍雖然常常為了顧全大局而委屈自己,但其在故事中已表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獨(dú)立性,幾乎是出于自愿原則對個人生活有著極強(qiáng)的掌控能力,這種掌控能力很大程度體現(xiàn)在公共空間與家庭空間的對立與置換。
家庭空間對于以陳思珍為主的女性角色來說是極為熟悉的,這一空間承擔(dān)著展現(xiàn)其日常生活的功能,太太思珍在這一空間中處理著各種家庭瑣事,其中除了與丈夫和父親這兩位男性在這一空間接觸以外,婆婆、志琴、陳母等女性角色則是這一家庭空間的表現(xiàn)主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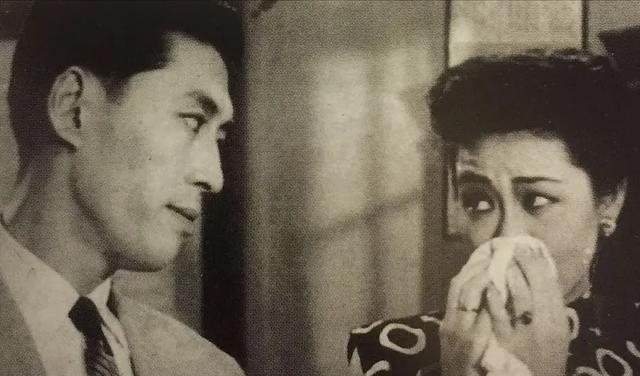
而以咖啡廳、銀行、公司、機(jī)場、律師事務(wù)所等地點(diǎn)為主的,代表消費(fèi)和生產(chǎn)的公共領(lǐng)域空間則往往是丈夫唐志遠(yuǎn)、楊律師等男性角色常常出沒之地。
前者家庭空間“具有封閉、限制、依附的性質(zhì)”,后者公共空間“具有開放、主導(dǎo)、生產(chǎn)”的性質(zhì),兩者起初以依附與被依附的關(guān)系存在,承擔(dān)著不同的敘事功能,以鮮明的“性別空間”差異構(gòu)建著性別話語之間的對立。

這與中國長久以來“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男女分工有著緊密的貼合度,性別與空間互為自洽。影片中的另一女性角色施咪咪被塑造成依靠迎合男人心理,甘愿充當(dāng)交際花的女性角色,她喪失了女性角色的家庭屬性及道德守則。
因此,她被放置于男性話語主導(dǎo)的公共空間,與西裝革履的唐志遠(yuǎn)一道,雖然彰顯著新都市生活面貌,但同時也由現(xiàn)代意識與消費(fèi)社會生發(fā)的如“婚外情”等價值觀所支配,并慢慢影響著家庭空間的平衡。

該影片的敘事空間平衡由丈夫唐志遠(yuǎn)的婚外情所打破,但“離亂之家”不同的是,家庭中的女性在遭受“侵犯之后”并非固守在家庭空間之內(nèi),而是以個體意識的覺醒橫跨兩個不同的空間話語。
《太太萬歲》所體現(xiàn)出的現(xiàn)代性便很大程度表現(xiàn)在太太陳思珍的跨空間行為上。當(dāng)施咪咪與其丈夫佯裝成兄妹打算以懷有身孕為謊趁機(jī)敲詐唐志遠(yuǎn)一筆時,太太陳思珍在丈夫的懇求下,出于“最后一次幫你”的立場出手相助,這一事件促使太太陳思珍從私人家庭空間進(jìn)入到公共空間領(lǐng)域,從苦難的承受者轉(zhuǎn)變?yōu)槁闊┑慕鉀Q者。

影片最后,觀眾矚目的“娜拉”盡管沒有成功出走,思珍原諒丈夫的同時也表明她重新回到了太太所屬的家庭空間中,而施咪咪也繼續(xù)游走于男性話語主導(dǎo)的公共空間。
但不能否認(rèn)的是,太太陳思珍確實(shí)以一己之力打破了以性別為依據(jù)劃分的空間屬性,在四十年代末的影像中建立起了具有鮮明獨(dú)立意識的都市女性形象。
觀念與空間性質(zhì)的錯位

在桑弧導(dǎo)演的作品中,上海摩登生活環(huán)境與上海市民生活旨趣成為了其作品的表現(xiàn)核心。另一方面,在這一類電影作品中,由都市生活環(huán)境派生出的對個人價值的重視又往往與傳統(tǒng)觀念形成對立關(guān)系。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家庭空間作為主要敘事場域,它不僅承載著創(chuàng)作者對彼時都市生活的態(tài)度,與此同時,又依靠家庭空間與個人空間的視覺差異詮釋著個人價值與傳統(tǒng)觀念的內(nèi)在沖突。

電影《不了情》的情節(jié)主要在嘉茵臥室與夏家兩個空間中展開敘述,與其說這兩個空間皆是對影片中主要人物的生活空間展現(xiàn),但在桑弧的鏡頭中,這兩個空間的鮮明對比卻蘊(yùn)含著人物價值觀的表征與對立。
《不了情》中的嘉茵以其獨(dú)立的個性讓觀眾印象深刻,這一角色與其他從農(nóng)村到達(dá)城市謀生的青年一樣,對城市的高樓大廈與無限機(jī)會保持著憧憬,但囿于經(jīng)濟(jì)條件或就業(yè)機(jī)會的限制,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在其身上的同時呈現(xiàn):

虞嘉茵身著長衫或旗袍,留著時下興起的卷發(fā),時尚又不失典雅,既符合其家庭教師的身份,又符合其身處的上海都市環(huán)境。
相比夏宗豫所在的洋房,其私人領(lǐng)域空間也顯得格外樸素,或者說,缺少例如旋轉(zhuǎn)樓梯、三角鋼琴、落地窗、沙發(fā)等現(xiàn)代家庭裝飾元素,但在這一空間中卻演繹著嘉茵這一女性角色承載的現(xiàn)代觀念。

嘉茵的個人空間在影片中大概出現(xiàn)了六次,她個人的情感思緒以及與夏宗豫的促膝長談成為了這六場封閉空間的主要情節(jié),對于個人前途的追逐與對姨太太這一男女關(guān)系的理性思考都與其所在的樸素?zé)o華的個人空間形成劇烈的反差。
可見,創(chuàng)作者無意于將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空間作為對立的兩個階層進(jìn)行表述,而是在上海這一都市空間中對個人領(lǐng)域與摩登家庭做了雙重的闡釋。

《哀樂中年》里的陳紹常僅年過50就被兒子與兒媳以“不忍父親辛勞”為由強(qiáng)留在家中安享晚年,這一主要情節(jié)表面上看是對家長里短的表述,但深層主題則是通過兩代人對養(yǎng)老、教育、婚戀話題的分歧,進(jìn)而呈現(xiàn)傳統(tǒng)觀念與現(xiàn)代意識的碰撞,這樣的碰撞體現(xiàn)在摩登家庭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視覺反差上。
正如有學(xué)者坦言:“桑弧電影影像中的公共構(gòu)造和空間,恰恰是理解中國現(xiàn)代性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diǎn)”,同時,“桑弧也不回避城市空間的另一面,影片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狹小的亭子間,正是上海底層市民居住空間的常態(tài)”。

在兒子建中功成名就以前,陳紹常帶著家人蝸居在傳統(tǒng)的上海民居中,他們擁有著普通上海市民的日常,恪守著傳統(tǒng)父慈子孝的倫理綱常,即使心有不愿,建中也要將第一月薪水交與父親,但從建中購買的第一條領(lǐng)帶開始,該人物所承載的現(xiàn)代都市生活氣息便愈加清晰。
汽車、洋房、收音機(jī)、沙發(fā)、洋表、咖啡館等成為了建中及其夫人的生活必需品。他們很快在物質(zhì)層面學(xué)到了都市空間中的生活法則,并同時以極其淺表的現(xiàn)代價值觀左右著日常行為。

例如不允許父親在街邊剃頭,為了保全顏面也不允許父親外出工作等等。而陳紹常、敏華雖然依舊保持著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作風(fēng),呆得最自在的空間莫過于學(xué)校、辦公室、家庭等傳統(tǒng)私人空間,但兩人的思想?yún)s比其物質(zhì)層面更具有現(xiàn)代性。
更為突出的一個例子是貫穿影片始終的墓地空間。影片開頭,早年喪妻的陳紹常帶著三個孩子來到陵園掃墓,墓地空間積淀著中國傳統(tǒng)的生死觀念,它不僅是對已故之人的緬懷場所,對年老之人而言更是一種對死亡的無畏與對生命的尊崇。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開頭不愿待在墓地而情愿到別處玩耍的孩子們卻在長大之后,特別是受到現(xiàn)代生活方式影響之后,仍然將這一承載傳統(tǒng)生死觀念的空間意義強(qiáng)加于父親。
然而,早年眷顧墓地空間的陳紹常在后輩視其垂垂老矣的時候,卻將墓地?fù)u身變?yōu)橐凰虝顺錆M著新生力量的學(xué)校。這種觀念與行為的不對等通過空間的差異表現(xiàn)出來,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感。

按上海歷史學(xué)者唐振常先生的說法,上海人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物質(zhì)形式的接受,明顯遵循著“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后繼則效”的典型步驟,但此中的“效”,在一個個都市之家中卻大多表現(xiàn)在物質(zhì)層面,這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
“都市之家”中的空間形象不僅對矛盾沖突的建構(gòu)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同時以性別作為空間劃定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加強(qiáng)了空間的文化意義。

其次,摩登家庭與傳統(tǒng)觀念、傳統(tǒng)家庭與現(xiàn)代意識通過空間性質(zhì)又呈現(xiàn)出某種錯位,成為了這一時期上海都市電影文本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影像特征。“每個具體電影文本中的空間既體現(xiàn)了導(dǎo)演個人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判斷,也體現(xiàn)了導(dǎo)演對社會的理解和評判。”
以桑弧為代表的都市電影人,始終以寬容的態(tài)度正視著上海都市的新舊交替與環(huán)境變遷,其寬容之處在于,他們并未將摩登家庭貶斥為物質(zhì)浮華的淵藪,也并未忽視普通上海市民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