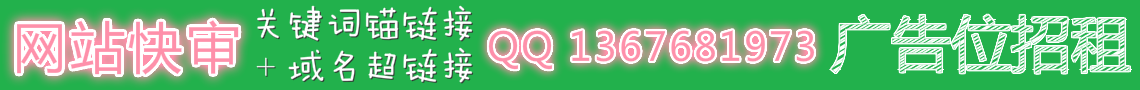后來,其他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行業都復蘇了,電影院卻遲遲沒開門。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原來電影不是人類生活的剛需。出品|博客天下大文娛組作者|屈露露編輯|丁宇2065年,“導演”已經被社會淘汰了。寧浩住在改裝后的房車里,開始種菜弄瓜,成了人們口中的浩子。賈樟柯獨守豪宅,變成了賈師傅,陪伴他的是一個機器人。那時候,人們不再需要電影,獲獎無數的導演被甩在時代之外。賈師傅和浩子也不例外,他們只能懷著對電影的熱愛,在電影博物館里追尋過去的記憶。

《地球最后的導演》劇照上述這些,都是電影短片《地球最后的導演》中對未來的想象,兩個失意的導演正是由賈樟柯和寧浩本人扮演。該片是B站上線的電影短片集《大世界扭蛋機》其中之一。導演徐磊給出的猜想是荒誕戲謔的——在未來,電影是那個“非必要不存在”的物品。除此之外,其他描寫人類未來生活的作品也集合在一起,陸續上線。世界如同一個巨大的扭蛋機,隨機掉落的短片里,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輪番上演。一群青年導演在寧浩和賈樟柯的帶領下,用各自的方式,假想了很多年以后,科技發展對未來社會和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雖然說的是未來、愛情、青春的主題,但講述的都是當下的奇觀。

火車駛向20652021年平遙國際電影節,《地球最后的導演》以閉幕影片的身份亮相,受到業內好評。短片戲謔式地設定了一個背景——2065年電影徹底死亡。拍了一輩子戲包攬無數國際性大獎的導演寧浩、賈樟柯失業了,他們雖然存在,卻早已失去聽眾,電影本身成了“非物質保護遺產”。一天,他們接到了同一個電話,要在他們二人之間選一個“電影非遺傳承人”。由此,賈師傅和浩子展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選爭奪戰。接受媒體采訪時,徐磊回憶起創作的心路歷程。拍完電影《平原上的夏洛克》之后,疫情來了,整個社會停擺,電影院關了門。后來,其他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行業都復蘇了,電影院卻遲遲沒開。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原來電影不是人類生活的剛需。既然如此,那必然有被淘汰的一天。不確定的市場環境、流媒體的沖擊……疫情3年,電影人成了命運共同體,承受市場風雨與環境的錘擊。

《地球最后的導演》劇照“因為我是干這個的,而且還剛入行,這行業就垮臺了,我就覺得還挺焦慮的。當時主要是為了緩解焦慮,就寫了這個故事。”徐磊的焦慮最終化為創作的動力,成為了故事的起點。作為壞猴子影業發起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的簽約導演之一,徐磊把《地球最后的導演》的想法告訴寧浩,對方覺得十分有意思,讓他趕緊寫。寧浩的電影中,“荒誕”是不可或缺的風格,所以看完《地球最后的導演》的劇本后,他很喜歡。他讓徐磊放心,自己會去說服賈樟柯。果然,收到劇本后,賈樟柯痛快地答應了出演。某種意義上,《地球最后的導演》是為寧浩與賈樟柯定制的作品。徐磊后來跟人說,要是沒有他們倆,這個故事就不成立。如果另一個視角來看,寧浩一路“瘋狂”到底,是最會賣座的文藝片導演,而賈樟柯是很多電影觀眾心目中,電影的代名詞。時代賦予在他們身上的符號意義,恰恰構成《地球最后的導演》的荒誕元素。短片中,每一處細節隱喻、影迷梗元素的使用,都是徐磊以未來視角構造了對電影輝煌過去的追憶。寧浩家沙發上的外星人玩偶,就是《瘋狂外星人》象征,而一尊菩薩像則是他的處女座《香火》的隱喻。短片開頭,在近代電影歷史重現演出館中,也出現了賈樟柯的《小武》《世界》《江湖兒女》等元素。《地球最后的導演》的結尾,兩位失意的導演穿著病號服走到沙灘上,在一處租看電影的小攤上,二人為選什么片僵持不下,不斷切換電影,直到畫面切到《火車進站》時,經歷了一系列較勁后的兩個人,終于和解了。(注:《火車進站》被認為是世界上誕生的第一部電影,也有人認為是《工廠大門》)

賈師傅和浩子共同選擇了放映《火車進站》《火車進站》的出現,像是一股平靜的力量,讓人心口泛酸。在黑白的、泛著顆粒的影像中,一輛火車呼嘯進站,在汽笛聲中停下軸輪,穿著中世紀服飾的男女在站臺上穿梭。“火車””在呼嘯聲中駛向2065年——一個完全不需要電影的年代。短片上線之后,故事新奇的設定,與當下電影窘境的相呼應,讓觀眾再次審視電影的處境。一位豆瓣網友這樣評價:“里面影迷梗超級多,真是電影愛好者的歡樂集市,最后看到《火車進站》很難不熱淚盈眶吧,一種電影人的孤獨與團結。”賈樟柯說,最后的《火車進站》是徐磊自己選的,但他跟寧浩都十分喜歡這個選擇。“就是你感覺到了電影最初發明的時候,那種人跟電影的關系,那種簡單的快樂的幼稚的電影,背后蘊藏著一種人類巨大的文明的提升和進步,我個人一直覺得,在人類諸多的藝術研究跟發明中,電影實際上是最偉大的一次跳躍。”徐磊幫助他們去感受、理解電影出生時代表的創造性,那是人類的一種超越,以及創造出一個新文明的喜悅,而這種喜悅其實帶給《地球最后的導演》一個悲傷的設定——“一種相對來說安慰的、溫暖的顏色。”一個扭蛋機的誕生寧浩為電影短片集《大世界扭蛋機》貢獻了很多個第一次。作為監制,他第一次當主演,第一次帶領青年導演們拍攝短片。

短片《殺死時間》中設定了未來人類生活《大世界扭蛋機》的項目很快開始了,經過不斷地豐富,最終分為“明日之后”“成長之前”“愛情之上”“青春之下”4個電影短片主題。包括《地球最后的導演》在內的“明日之后”篇章,探討未來社會中人與科技、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寧浩表示:“明日之后”中每一個導演最后表現出來的都是通過對未來的遐想,來關心人的處境,關系到我們對于自身處境的想象。2020年冬天,曾贈把自己關在家里,與外界沒什么交流。在社交平臺上,她回憶了當時的狀態:“很長時間之后我審視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似乎很久都只說過這十句話了:你好,再見,謝謝,抱歉,好的我盡快改,我在開會晚點聯系,是本人,放門口吧,我掃哪兒付,不好意思讓一下……”曾贈說,她在生活中是一個連接電話、聽微信都十分恐懼的人,但矛盾的是她又時常感到孤獨。這讓她開始思考,科技到底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更遠了,還是更近了;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更簡便了,還是更難了?這些思考最終構成了短片《你好,再見》。曾贈說:“我有我自己的答案,但是這只是我自己相信的答案,它也就是這個片子創作的邏輯。”

短片《你好,再見》中設定,人與人之間只有10句話的通話權限《一一的假期》導演吳辰珵關注的是“養老”議題。創作時她問了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在一個人口出生率變低,老齡化變嚴重,但效率至上的時代,如果它發展到極致,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因為吳辰珵本身就喜歡童話,所以在為故事尋找落地支點時,她決定以兒童視角切入,將童話與科技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而言,《一一的假期》并不是一個邏輯簡單的低幼故事,它甚至是有一點暗黑的詰問——“對于一種極端化的社會現象的反思”,故事內核是殘酷的。片中構想了一個效率至上、高度精細化的世界,這里科技發展迅速、人類極速繁衍,導致資源匱乏,人類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掙取生存成本,老年人成了最孤獨的群體,也成了家庭中的“難題”。為了給一一即將出生的妹妹騰出住處,姥爺被家人送去了虛擬養老院。人類在一個效率極其至上的年代,人和人之間的親情甚至都會被割舍掉。寧浩認為,《大世界扭蛋機》中每一個導演都展現了他們的想象力以及他們獨特的性格,這些都讓他非常欣喜。同時,短片形式又讓導演們尋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式,并且印證了自己的想法。“后生可畏”的沖勁兒從吉光片羽的靈感到成為故事核,青年導演們花費了很長時間與精力去打磨。但把一個故事核濃縮為二、三十分鐘的完整短片,困難是肉眼可見的,一切都要搶時間。《你好,再見》前期策劃了2年,但拍攝時間只有6天。曾贈用“大工地”去形容片場。現場沒有實景,他們只能一邊拍戲,一邊拆舊景,一邊蓋新景。地鐵上的戲是最難拍的,因為涉及到群演轉場等現場協調,幾乎在一個不可能的時間下,這部短片才被完成。《一一的假期》拍攝時周期相對富裕一點,9天,但這也讓吳辰珵時常感到捉襟見肘。短片今年1月中旬開機,天氣十分寒冷,她在天氣狀況和場景量都很極端的情況下,完成了拍攝。

《一一的假期》中,虛擬養老院可以讓人們選擇回到任何年代,但實際上老人們被禁錮在虛擬的世界中讓她印象最深的是拍攝上世紀90年代的場景戲。按照場景要求,應該是一個艷陽高照的溫暖環境,但拍攝前兩天開始下大雪,劇組的工作人員全去人工鏟雪去了,等到景打掃的差不多了,她為了營造光線,幾乎把器材公司的燈都借空了,才把艷陽天的氛圍搭出來。對于《地球最后的導演》徐磊來說,怎么把兩個第一次擔當主演的大導演,調和進一個世界里是一件難事。時間同樣緊迫,周期只有8天,還要配合寧浩和賈樟柯各自的工作時間。“兩個人同時在現場的時間可能只有兩三天”,這意味著每一步拍攝統籌都要打著算盤來。短片中,寧浩和賈樟柯要演2065年退休后的自己。為了減少臺詞困難,徐磊特許他們用山西方言去演,在不影響劇本主線的框架下,進行自我發揮。很多戲和臺詞都是大家碰出來的,寧浩和賈樟柯經常互相飆戲。短片中,二人在酒吧爭風吃醋的臺詞都是他們的自由發揮,賈樟柯那段“獅啊熊啊豹啊”的得獎發言就是他的設計。寧浩聽徐磊說賈樟柯給自己“加了不少戲”后,也不甘落后,決定加上了給小朋友講戲的片段。盡管片場里二人經常上演老頑童般“爭強好勝”的戲碼,但寧浩認為跟賈樟柯演對手戲非常開心。“我覺得賈導確實是太放松了,我是技術型他是自然派,所以我們兩個確實還是很努力的,認真的才能搭在一起,我們演戲很認真的。”

《地球最后的導演》中,得知電影非遺申請項目沒有通過后,賈師傅和浩子急火攻心,被送去急救“喝羊湯”那場戲上,徐磊曾經表達過自己的創作意圖:“(中國傳統文學中)試探一個老將到底能不能出戰的方式,就是看他能不能吃飯,看看他勁還大不大,能不能拉開弓。”所以短片中,他設置了二人比力氣、比看誰能吃的戲份。賈樟柯知道這個想法后就出主意:“你說我這么說行不行,‘你懷疑廉頗也不能懷疑我’。”對于“出演自己”這件事,寧浩和賈樟柯不約而同地認為,短片中都是虛構的“他們”。寧浩說,《地球最后的導演》中的自己和現實生活中的他差別很大。比如,他的確喜歡侍弄花草,但是沒有想過住在房車,原因是蚊子太多了。他也不知道以后會不會像浩子那么能折騰,但唯一可以確定地是,他老了肯定還是喜歡看電影。和寧浩一樣,賈樟柯對電影的未來并不悲觀。在他看來,也許從公共層面,電影會消失,但并不意味著私人層面的消失。他甚至做出了一個可愛的設想,也許未來電影的播放形式和載體會發生變化——“我們每個人的視網膜或者眼睫毛就有一個播放器。”但到那一天,他不會再拍電影了。賈樟柯說:“我覺得每個人有自己喜歡的電影形式,我的形式可能就保留在現在通過放映、投影、集體的觀看,來看一部電影,如果這種形式改變了,可能我也就沒興趣拍電影了。但是我相信人類不存在地球上最后的導演,一直會有導演,只是電影的形式,最后可能變得我們非常陌生了。”

《地球最后的導演》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