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員美女,尺度生猛,再看不到這么有特色的古裝劇了
能穿越時光成為經典的作品,必然有其過人之處。
比如,18年前的《大唐情史》。
這部劇能有8.1分,美女多、尺度大、風格新都是主因。

我們先來說美女。
那個時候還不流行什么網紅臉,劇中從高陽公主到玳姬、從楊妃到武則天,都是各具風情、絕無雷同。
不少看過《大唐情史》的觀眾,將這部劇奉為“美的啟蒙”。
作為跟僧人辯機談情說愛,唐朝皇室丑聞的主角,高陽公主在過往影視作品中多被“妖魔化”。個性驕縱跋扈、生活奢靡混亂,是她給人的主要印象。
但在《大唐情史》中,觀眾看到了一個更“完整”的高陽。她的叛逆、瘋魔背后,是對命運的不甘和抗爭。

高陽公主出場前,劇中借長孫嬙兒(印小天飾)之口,發表了一通類似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中的言論,總結何謂真正的美女。
一番鋪墊后,得出結論“最美的當然是高陽”。

而沈傲君扮演的高陽公主,也的確撐得住人物設定。眉目如畫、雍容嬌艷,尤其是屬于她本人的那份溫婉、嫻雅,更是對高陽公主舊有印象的駁斥。


作為高陽公主的生母,玳姬(張彤飾)的美則是藏不住的風韻撩人與蝕骨銷魂。
開篇“畫像”一幕,就已經讓觀眾先于李世民被“征服”。

繼而,在秦王赴宴時,她撩開帷幕、妖嬈出場,行動之間更是將魅力釋放到極致。

只有這樣的美,才能讓秦王危機重重中還不忘對玳姬表白、明知酒中有毒還甘愿飲下的情節設定,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但玳姬最美的不是她的妖嬈,而是她不屈服于權勢,不耽溺于榮華,只肯為情低頭的傲骨。正是如此,才讓李世民對她難以割舍、欲罷不能。


同是被收納的“政敵家屬”,楊妃(顏丹晨飾)則是溫柔和順。

作為隋煬帝之女,前朝的亡國公主,楊妃知道自己的身份有多敏感。因此,想要在新朝君主的后宮中安身立命,僅靠帝王的寵愛遠遠不夠。她必須證明自己“無害”,以此消除唐皇君臣的顧忌。
楊妃為自保而不得已的隱忍,與顏丹晨清麗、秀雅的樣貌相融后,變成了這個角色身上的美、慘屬性,很容易引得觀眾憐惜。

劇中另一個大美女,是飾演武則天的秦嵐。
從十四歲因“容止美”被召入宮,賜號“武媚”這點,就知武則天曾經有多美。那時秦嵐剛畢業,雖然是初次拍戲,但她卻抓準了角色特點。
比如面對李世民時,她展現的是自己的弱勢,看起來十分楚楚可憐;

與李治在一起時,她展現的是自己的柔情,讓對方相信愛他不可自拔;獨處時,又將心里的欲望,借用眼神呈現給觀眾看。


除了高陽她們之外,劇中長孫皇后(趙倩飾)的端莊大氣、文成公主(葉小閔飾)的俏麗甜美,同樣也是養眼的存在。


再來說尺度。
單是將高陽公主和辯機和尚的“風月案”作為主線,就已經印證了主創的大膽。《大唐情史》這個劇名,也透著幾分宮闈秘聞的香艷色彩。
更重要的是,它還不是“標題黨”,是真的有料兒。
跟李世民相關的影視作品不少,有幾部敢上來就讓他“開船”?而且還是強制愛。
開場夠猛,后面也沒泄勁兒。
高陽和辯機之間沒什么點到為止,該開車時就開車,不該關燈的時候堅決不關。情到濃處,滿心的愛戀自然就成了出口的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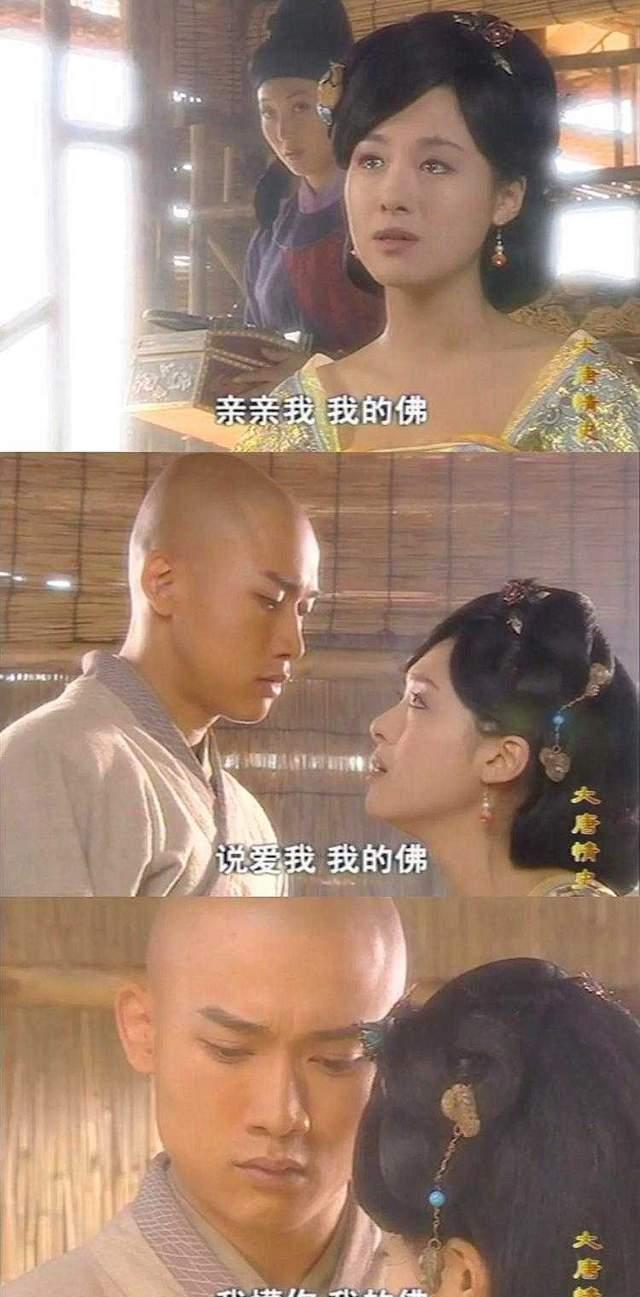

高陽和哥哥李恪之間,因為劇中的曖昧朦朧,多了幾分CP感。有看過本劇的觀眾,直到現在還站這條線。

武則天和李治這一對兒,也是各種生猛。雖然相關戲份不算多,但足以讓觀眾相信,他們是抓住一切機會,用實際行動表達誰也離不開誰。

李承乾和稱心的故事我們不陌生,但讓當事人這么吐露心聲的,《大唐情史》之前沒有,之后更是沒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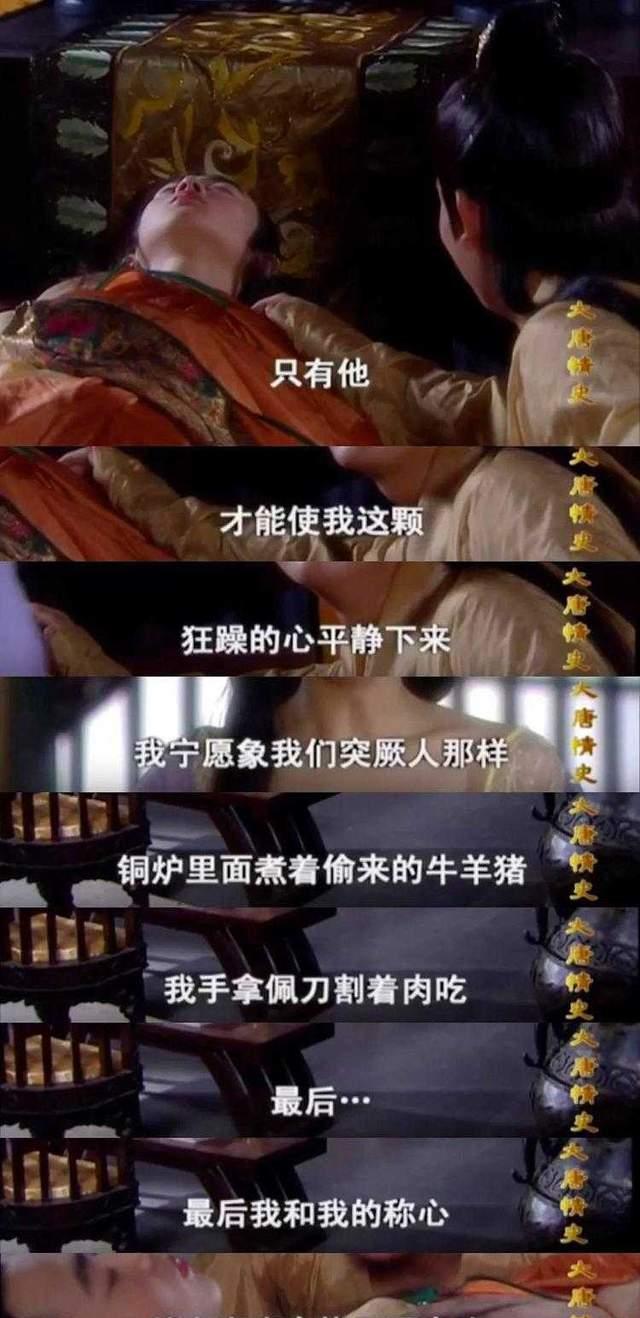
雖然“大”場面多,但因為有著足夠的情感鋪墊,所以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不會讓人覺得油膩、低俗。
這就是風流和下流之間的度。
最后來說風格。
李少紅的《大明宮詞》以“莎翁風”令人印象深刻,《大唐情史》走的也是這個路線,透著戲劇、詩歌的浪漫、唯美。
我們印象中,古人的情詩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這樣式的。
但劇中長孫嬙兒寫給高陽的情詩,卻是“圣潔的白蓮,我愁思著美艷……我安能忘卻你嫵媚的形骸”這種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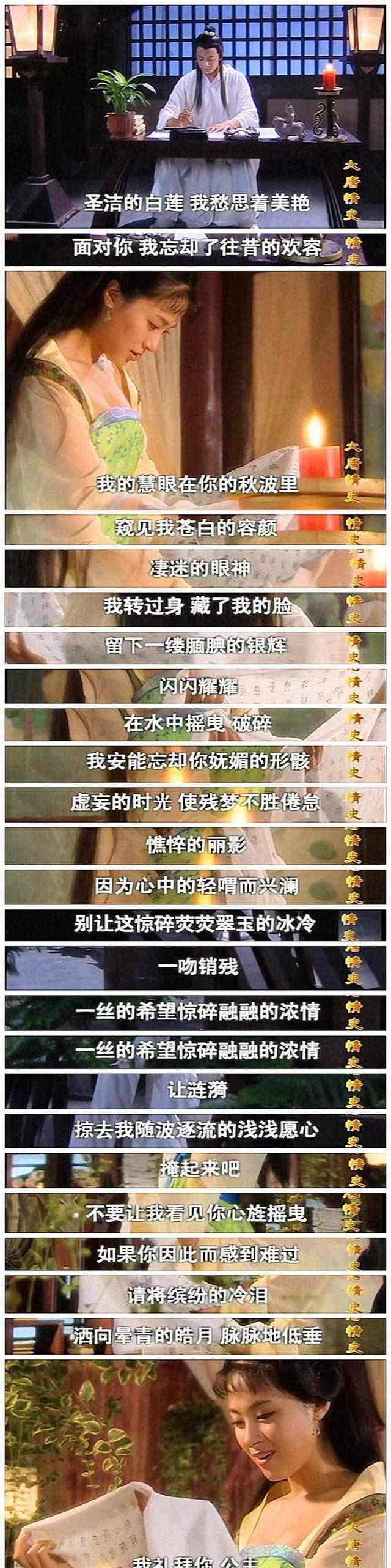
辯機看到高陽哭泣時說“我無法阻止你的眼淚,就像我無法阻止一場大雨,一場山洪”,高陽依偎著辯機時說“翻書的聲音真好聽,是你,還是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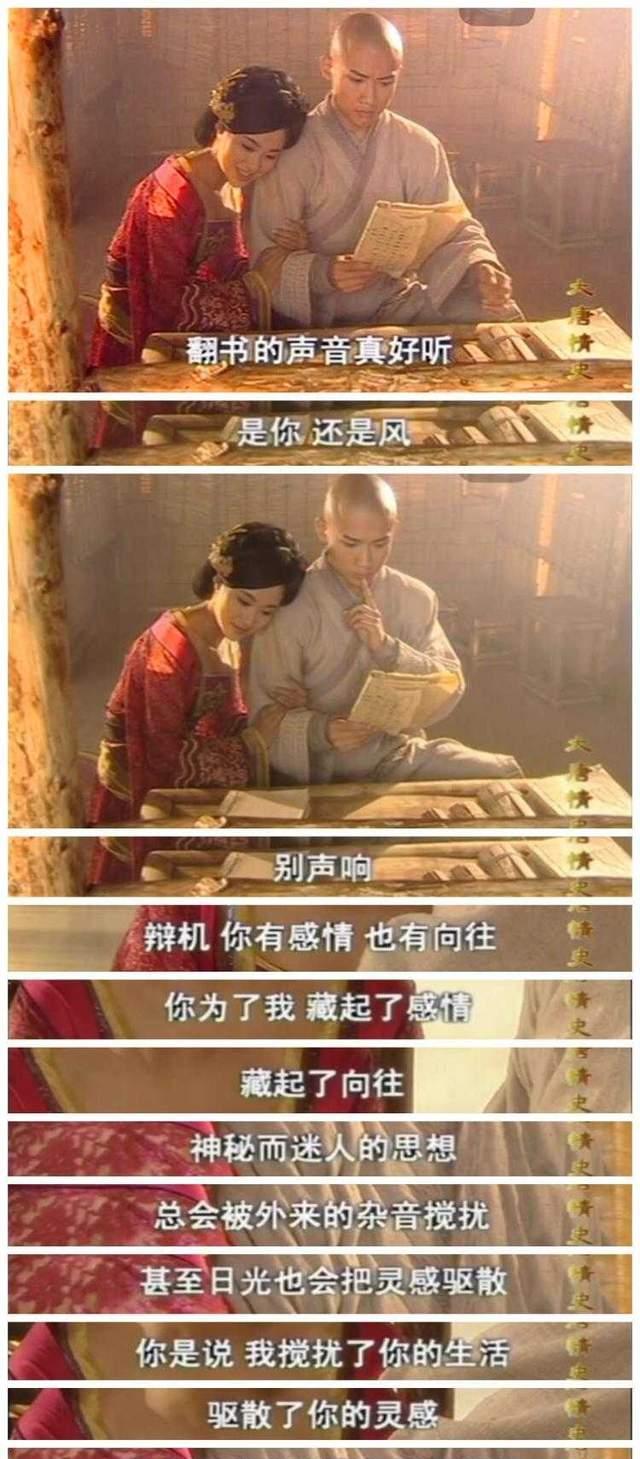
兩個人最后生死訣別時,辯機還即興來了一段“詩朗誦”,借用萬物自然與佛陀,表述自己對與高陽相愛的無怨無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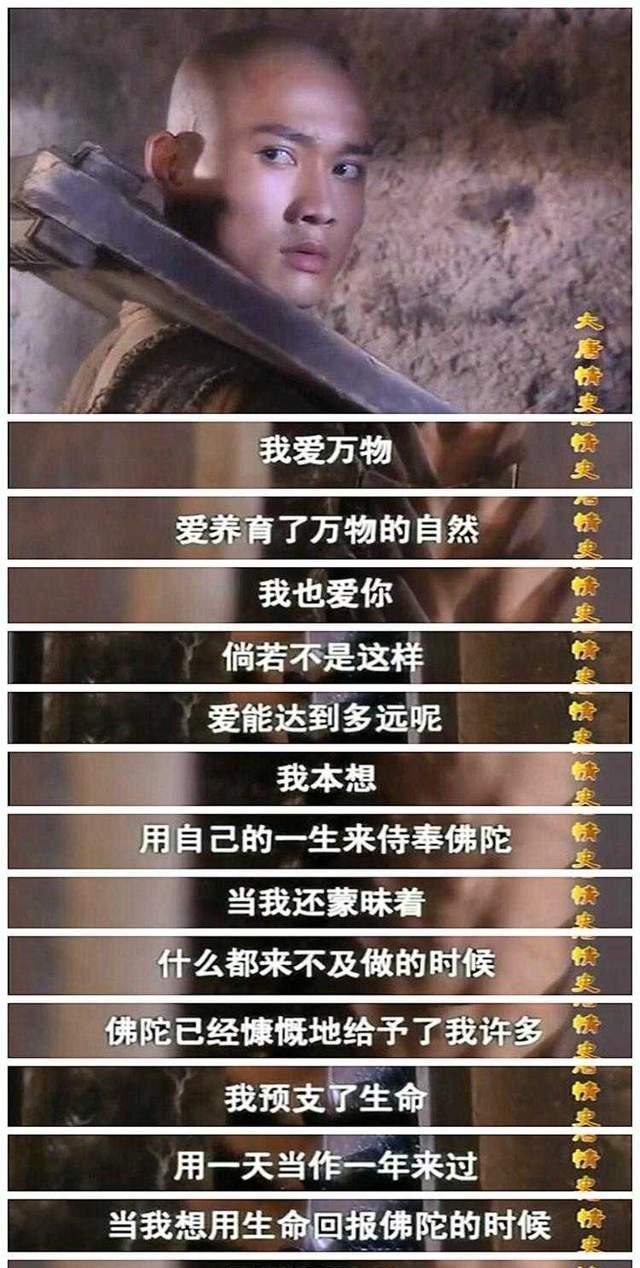
除了這三個主因,《大唐情史》還贏在立意和格局。
多數宮廷言情劇,都被困在勾心斗角、爭風吃醋中。但《大唐情史》從策劃之初,就是將“以史為鑒”作為核心。所以,劇中既有貞觀盛世的繁華,也有后宮的傾軋、朝堂的黑暗。多角度、多面性的展示,讓整個故事更加豐富且貼近真實。
同時,劇中公主、皇帝亦或是佛門中人的放不下、求不得,讓觀眾看到了一群被生活羈絆、困縛的普通人,繼而與之共鳴、共情。
以上相加,才最終成就了《大唐情史》在國產劇中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