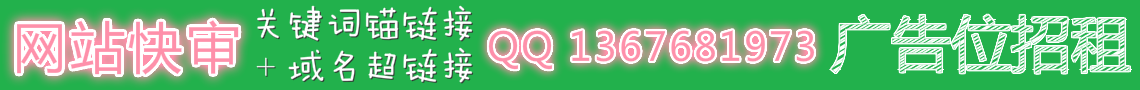戛納電影節落幕。
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是時候復盤了。
不是主競賽里大家最關注的那幾個大獎,而是一個小小的獎——
第一屆#TikTok 短片競賽#。
將選出TikTok應用中創作、時長在30秒到3分鐘之間的垂直短片參與競爭,由單獨的短片評審團進行評審。

互聯網內容平臺和老牌電影節的合作。
沒想到出了個風波,頒獎前3天,該單元評審團主席潘禮德宣布辭去職務。
在對評審團的獨立性和主權持續產生分歧后,我決定辭去該評審團主席的職務。

△ 潘禮德:紀錄片《輻射》入圍柏林主競賽,柬埔寨首位獲奧斯卡提名的導演
為什么?
印象里,老貴族戛納和互聯網新貴一直有矛盾。
2018年戛納明令禁止明星在紅毯自拍,同年拒絕奈飛出品的電影參加主競賽單元。

既然不待見,為什么還要合作?
既然合作了,為什么主席要突然辭職?
原因比我們想象得要更復雜。
傳統院線和互聯網平臺之爭仍在繼續。
只不過又進入了下一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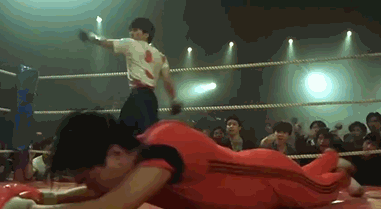
01
電影節從來不只是電影藝術的殿堂,也是流量池。
在TikTok之前,戛納的“外圍”一直都是開放合作的。
最明顯的例子,紅毯。
能走上紅毯的明星,大致可分為五類:
參演提名作品、官方邀請、品牌受邀代言,還有賣片的和硬蹭的。
除第一種“名正言順”,其他都裹挾在巨大的商業利益之下。
早年的趙濤到今年的谷愛凌都是官方邀請,前者因為作品曾四次入圍主競賽攢下了人品;后者則是流量新秀和知名度代表。
曾經范冰冰代言的巴黎歐萊雅和蕭邦珠寶都是戛納的贊助商,出席屬于工作范疇。拿下“最佳妝容”和“最佳著裝”的李宇春當然也有古馳的加持。
龍袍、花仙子、黑天鵝、紅斗篷……

△ 圖源:視覺中國
作為名利場,紅毯意味著曝光度和商業價值。
“中國毯星”爭奇斗艷也曾是飽受詬病的一大盛景。
《畫皮2》在戛納辦發布會,楊冪長時間逗留被驅趕;井柏然馬思純跟著《盜墓筆記》去戛納宣傳,因疑似邀請函有問題,遭到工作人員阻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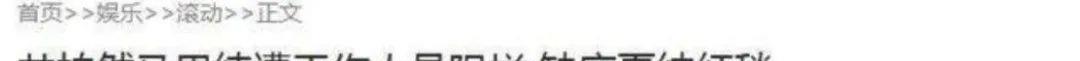
更不用提各路硬蹭的神仙,當然,這需要提前購買“門票”。

△ 圖源:視覺中國
除了名流圈競技,電影節也是對熱點議題、社會運動回應的窗口。
女性平權。
哈維·韋恩斯坦性丑聞事件后,第71屆影展紅毯被MeToo運動點燃。
由凱特·布蘭切特牽頭,82頂尖女演員和女導演發起抗爭行動,向性騷擾宣戰。

△ 圖源:視覺中國
福茂也簽署了備忘錄,承諾將致力于在電影節上實現性別平等,并開通“舉報性騷擾”的熱線電話。
今年,還有澤連斯基視頻連線戛納現場發表講話。
從《火車進站》聊起,《大獨裁者》《現代啟示錄》《鋼琴家》《羅馬,不設防的城市》《陸軍野戰隊》《美麗人生》《無恥混蛋》……
電影節是一套圍繞著制作、發行、放映的生態系統。
外圍的名利場是造勢。
對觀眾,電影節采用的是申請制,有的嚴格分級,有資格的觀眾在放映前也要排長隊,這賦予了觀影一種朝圣般的儀式感。
內圍的電影才是核心。
和奧斯卡評選的商業化和政治正確不同,戛納更看重作者性和先鋒性。
電影節作為導演的培養皿,挖掘并培養未來可期的“嫡系導演”。
不羈前輩步履不停。
新浪潮之父,耄耋老人戈達爾仍在試圖開拓電影邊界。
《電影社會主義》的預告片將原片80倍速播放,被譽為“真實預告片”;《影像之書》幾乎完全由舊電影、歷史畫面剪輯而成,像極了up主的二創。
實力中生代穩中求進。
簡·坎皮恩的《犬之力》用西部片的殼獨辟蹊徑,奉俊昊的《寄生蟲》打通藝術和商業的通道。
生猛后輩狂飆突進。
“戛納親兒子”澤維爾·多蘭的《只是世界盡頭》拿評審團大獎;朱利亞·迪庫諾的《鈦》大殺四方奪金棕櫚。


不僅是電影形式和內容的新,也是電影模式的“新”。
2017年,戛納電影節增設了VR展映單元,岡薩雷斯·伊納里圖6分鐘VR短片《肉與沙》亮相,讓戴上VR眼鏡的觀眾直接體驗難民的處境;2019年,戛納成立了以VR為代表的新型沉浸式媒體單元,助推VR產業發出更大聲音。
面對流媒體的沖擊,福茂也很有自信。
反問現場媒體:
流媒體發展到現在有沒有培養過什么優秀的導演?
媒體沉默。
戛納并不保守,也不怕新鮮血液的注入。
因時而變的規則,深厚的底蘊和盤根錯節的社交網,是電影節生生不息的底氣。
那么作為電影投資新貴的流媒體,到底要怎么爭,爭什么?
02
“我個人覺得不應該把金棕櫚大獎頒發給一部大銀幕上看不到的電影。”
第70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主席阿莫多瓦,就這樣給奈飛出品的《羅馬》判了“死刑”。
這話乍聽起來極端,像是出身論歧視。
富商之女《羅馬》,就是不敵一品大員電影公司的嫡女能得皇帝青睞。
明明戛納最重要的一條選片原則是:
任何人拍攝了一部超過一小時的電影,都有權報名并一定會被選片委員會看到,無論這部影片來自哪里,無論拍攝者有沒有名,無論使用如何簡陋的設備。
——《上觀新聞》 福茂采訪
以質量來說,《羅馬》絕對夠得上主競賽的標準。
重建的羅馬街道,私人的黑白影像,溫柔女仆的悲傷絮語。
之后在威尼斯、金球、奧斯卡連獲大獎,像片中的海浪一樣一波波涌來,足以見其質量。

關鍵詞藏在阿莫多瓦的話里,
“大銀幕看不到”。
往回倒帶,曾由奈飛出品的奉俊昊的《玉子》和諾亞·鮑姆巴赫的《邁耶羅維茨的故事》繞過法國院線,在自己的平臺上全球同步首播。
法國發行商、電影院質疑其參賽資格并施壓戛納組委會,要求將作品從主競賽單元中除名。
從利益分配看,這是一場零和博弈。
流媒體一來就打破游戲規則,自己投資制作、流媒體平臺發行和放映,自產自銷。
雙方拉鋸的焦點,就是
影院的窗口期。
影院窗口期在各個國家都不相同,法國政府介入的文化藝術保護機制有嚴格規定,從院線到流媒體的窗口期長達36個月,北美一般默認為3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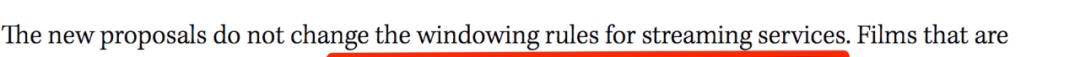
△ 新提案里,法國院線也沒放松對流媒體的制約
為什么要這么久?
對創作者和院線的一種保護方式。
一旦線上影院同步上映,就會滋生以盜版為主的一系列問題,影院利益大大受損。
而且電影規格和網絡平臺的觀看環境迥異,導演針對大銀幕的視聽設計也會大打折扣。
奈飛顯然不想等這么長時間。
自己花了高昂的制作經費投資發行的電影,卻要延遲那么久才能讓訂閱用戶享用,也太離譜了。
當年,這樣一個“先斬后奏”鬧得電影節猝不及防,雖然經過多方協調,保住了兩部影片的參賽資格,可奈飛卻上了戛納的“黑名單”。
2018年直接增添新規,只有在法國院線公映過的影片才能在主競賽單元參賽,這讓奈飛包括《羅馬》在內的5部電影直接失去了競爭資格。
據說當時戛納大銀幕只要出現奈飛標志,現場就會噓聲;
更抓馬的是,《玉子》第一場媒體放映,盧米埃爾電影廳的幕布機械出故障,全場兩千多名記者在銀幕被遮擋三分之一的情況下硬看了將近六分鐘開場,這次放映事故被奈飛視為“戛納的報復”。

奈飛要面對的不僅是傳統院線,還有同行。
《天鵝絨金礦》的導演托德·海因斯是個絕對的電影主義者,可他由亞馬遜發行的新片《寂靜中的驚奇》卻入圍了戛納主競賽。
他直言道:
“亞馬遜和奈飛的那幫人可不一樣,他們是真正的影迷。”
原因?
亞馬遜遵守行規,先院線,后平臺。
2017年亞馬遜發行的《海邊的曼徹斯特》就已經因為先在影院上映,窗口期后才轉到Amazon Prime Video放映而嘗到了奧斯卡的甜頭,拿下了最佳男主和最佳原創劇本。

Vue International電影院的CEO表示:
“電影被定義為在影院上映的電影——所以它是一部真正的電影。奈飛和其他流媒體服務屬于家庭娛樂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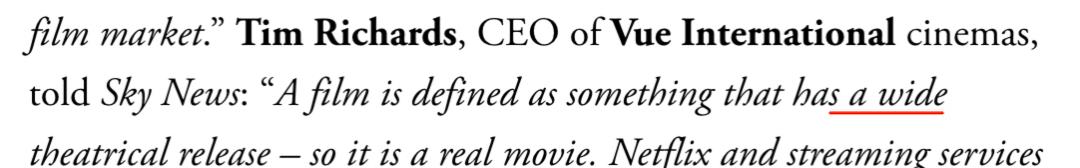
流媒體和電影院之爭,
是未來電影形態和渠道的秩序之爭。
誰也無法斷言未來,說清誰對誰錯。
像2019年,馬丁·斯科塞斯為奈飛站臺,因為它是新片《愛爾蘭人》唯一資方。
這樣一個僅靠票房難以收回成本的電影,一直沒找到投資,如果不是奈飛,馬丁根本沒有機會把它拍出來。

同年,Disney+上線,同樣是自產自銷,來分“傳統流媒體”的線上蛋糕。
一邊,斥巨資拍“最電影的電影”,打造品牌立人設。
一邊,反守為攻,利用IP優勢拓展疆域。
只有被拋棄的電影院,在疫情和流媒體的沖擊下風中蕭瑟。
但這權力的斗法,卻逐漸從開始的姿態強硬,生拉硬拽。
逐漸變成了一場你來我往,推拉游移的太極。
03
TikTok歐洲區總經理里奇·沃特沃斯的發言給這次合作下了定義:
“永遠改變全球電影格局的標志性時刻”。
合作中,TikTok前期給資金、中期用網紅引流;戛納給紅毯、后臺和影人獨家采訪。
看似是一場你負責流量,我負責藝術的公平交易。
但潘禮德的辭職聲明里有兩個關鍵詞:
獨立權、主權。
原來這才是流媒體與大制片廠的博弈核心。
結果,兩者斗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
上個月,因為發布了糟糕的第一季度收益報告,奈飛股票10年來首次出現暴跌。
和被迫裁員一樣可怕的,是下個季度預估痛失200萬用戶。

△ 圖源:FINANCIAL TIMES
怎么辦?
奈飛一貫特色,因時而變。
預備改制,妥協,遵守影院窗口期規則,雖然只有45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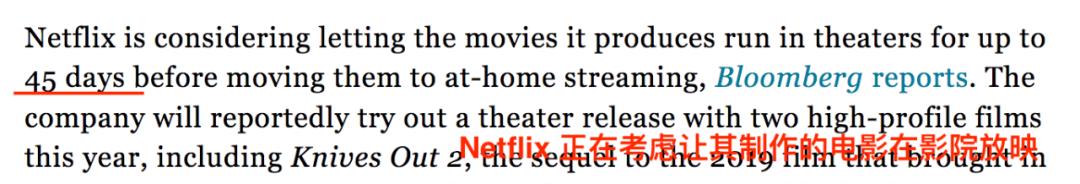
電影院不僅是觀影的儀式化場所,更是熟人社交的需要。
也只有在影院上映,才能擴大大片的知名度,讓觀眾不至于在流媒體的海量信息中迷失。
在流媒體時代,電影院有潛力幫助所有內容所有者,包括像奈飛這樣的流媒體平臺,突出他們最好的內容,并將他們的平臺推銷給他們的核心觀眾。
——《財富》采訪電影行業分析公司 Gower Street 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Dimitrios Mitsinikos
面對歐洲市場,
奈飛以“硬骨頭”法國為突破口。
與法國電影協會簽署了為期3年的協議,將其在法國年收入的4%,至少4000萬歐元,用于資助將在法國影院上映的法國或歐洲電影,其中至少有3000萬歐元投于法語電影。
所有這些電影都將在法國院線首映,并將在15個月后的奈飛上線。
影院有7個月的獨家窗口期。
如果這樣,奈飛未來在本質上就是流媒體+電影制片廠。

反觀Disney+的業績卻穩步增長。
相比于奈飛會員最高等級每月20美元,最高套餐14美元的迪士尼有著明顯的價格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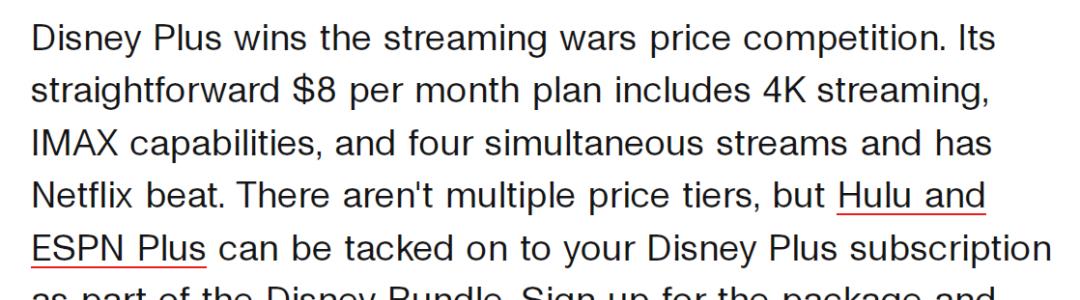
站在歷史與未來的十字岔路口,他們走上了對方的道路。
經歷了2020云戛納的電影節,2021也采取了線上線下的模式。
云電影節的概念也在不斷被推廣。
等級制度,排片表,虛擬放映室,時間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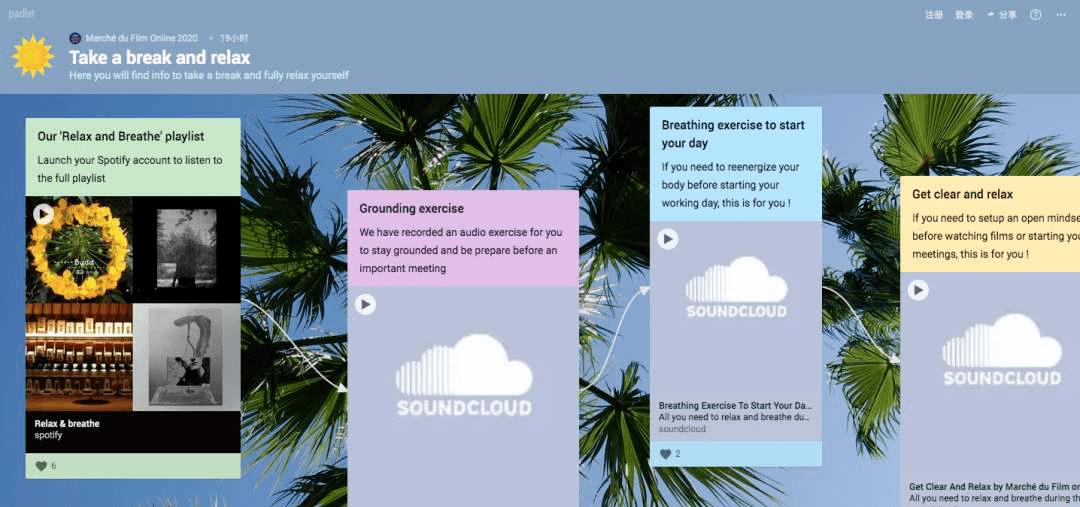
特殊情況下,影院的儀式被云平臺的時間限制擊得稀碎。
回到開頭,這次的TikTok短片競賽猶如過山車般又發生了戲劇性反轉——
潘禮德回歸頒獎禮。

為什么吃回頭草?
因為,談攏了。
開始,TikTok高管想干預評審團的審議,甚至將陪評團選出的一些短片替換為TikTok更喜歡的主題。
最后兩邊各選一部,作為評審團和TikTok最喜歡的片子頒獎。
面對評審團選出來的片子,TikTok高管表示評審團選的短片違反了比賽條款,需要取消參賽資格,要求就選TikTok中意的那部。
這才導致潘禮德辭職。
后來經過協商,TikTok投降,“主權”回到評審團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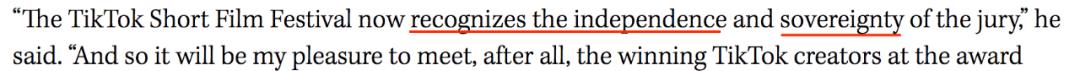
最終獲獎影片仍有兩部:
來自斯洛文尼亞導演Matej Rimanic的《飛機上的愛情》(
Love In Plane Sight
),愛情故事;和日本導演Mabuta Motoki的《砍樹可以嗎?》(
Kitte kitte iino?
),環保和傳統題材。

高創意,低成本,是這類短片的核心訴求。
潘禮德在頒獎時表示:
只有一分鐘美麗、詩意的電影,講述了從生活中的困難到傳統、幽默、痛苦、愛情的一切,要在一分鐘內完成并不容易。
而TikTok法、比、荷三國總經理Masure的致辭也耐人尋味——
以數據為核心。
引用44個國家的參與數據和全球45億人的觀看數據,為TikTok是個“講述故事和創造情感的絕佳平臺”背書。

線下還是線上,大眾還是專業評委,作者表達還是商業性。
這些伴隨著電影多時的問題,今天又出現了新的心態。
未來的電影會走到那個方向?
仍在掙扎,徘徊。
但不管往哪走,前提是你有選擇。
如果連電影院都還回不去,那么討論電影該往哪走,都還太遙遠。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助理:西貝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