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nèi)晕吹弥瑒⒁喾圃谔焱r(shí),到底犯了什么錯(cuò)。”
這是天仙新劇《夢(mèng)華錄》的觀眾熱評(píng)。
沒(méi)人嘲土味,也不需要補(bǔ)后半句——“才會(huì)被貶下凡”,忒多余。

不深刻,卻也多少解釋了這幾天你被刷屏的原因——她,飄回來(lái)了。
時(shí)隔十六年,劉亦菲再演古裝劇,率先帶回了什么?
一些基本常識(shí)。
原來(lái),古偶就是要美人的。
原來(lái)真美人并不需要去捍衛(wèi)她的美。
“絕色”二字,不再僅配角和粉絲可見(jiàn)。臺(tái)詞與下一秒晃進(jìn)鏡頭的面容對(duì)上的爽感,竟然有點(diǎn)陌生。

“鄉(xiāng)野村婦”也不過(guò)成為又一個(gè)“平平無(wú)奇”梗,忙都不用忙。
美女解放了粉絲,粉絲解放了路人。
苦“古丑”久矣的內(nèi)娛人,近乎報(bào)復(fù)性地,一路狂歡兼哀鳴。
開(kāi)分打出8.3,后又飆升至8.8。
一周過(guò)去依然堅(jiān)挺,近22萬(wàn)人,捧出了2022上半年第一高分劇。

當(dāng)人們從古偶最不該出問(wèn)題的問(wèn)題里脫困,才終于能探討更上層的東西:
比如,它憑什么?
比如,劉亦菲對(duì)劇的加持,顯而易見(jiàn)。那,劇對(duì)于劉亦菲呢?
毒藥電影多年,下凡仍是靈丹。
僅僅是賽道對(duì)了么?
不。
要飄說(shuō),《夢(mèng)華錄》和劉亦菲,是限定的爆款,誰(shuí)也離不得誰(shuí)。

甭管劉亦菲過(guò)去在天庭犯了什么罪。
一定不是因?yàn)檎剳賽?ài)。
因?yàn)樗癖粣?ài)情開(kāi)除了的。
或者說(shuō),她不像一位會(huì)鬧思凡的仙女。
她的美似乎一直沒(méi)有撩動(dòng)情欲的部分。
美得獨(dú)美,服務(wù)于cp時(shí),你驚為天人,膜拜就好。
《夢(mèng)華錄》的第一成功之處,其實(shí)是打破了這個(gè)禁錮。
它竟然使“天仙談情”這件事,成立了。
一條“懂得都懂”的標(biāo)志:
在當(dāng)下,一部主打女性互助、女主女二女三各有風(fēng)格、時(shí)常貼貼的劇里。
觀眾目前仍沒(méi)有拋棄官配cp。

并且,嗑學(xué)家們對(duì)男主顧千帆(陳曉 飾)和女主趙盼兒(劉亦菲 飾)的“顧盼生輝cp”上頭之勢(shì),似乎還愈演愈烈。
這已能說(shuō)明一些問(wèn)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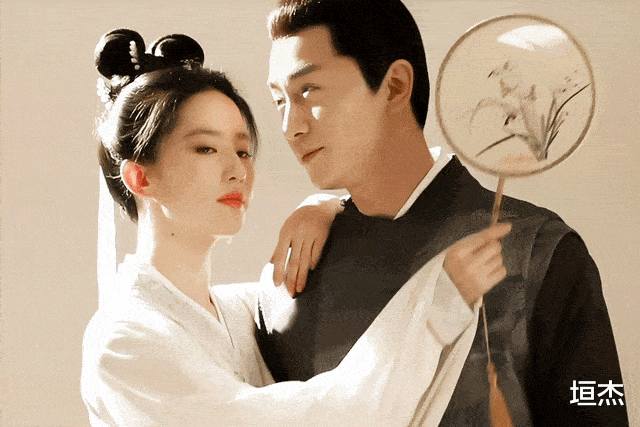
男俊女美,為bg(男女向cp)添光也不稀奇。
新鮮在于,這一波,大家確實(shí)是用成年人的嗑法,在嗑成年的戀愛(ài)。
這是劉亦菲的罕事。
在我們更年少時(shí),或者多少也嗑過(guò)天仙的經(jīng)典cp,比如遙靈、或是段譽(yù)王語(yǔ)嫣、表哥表妹。

但,它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人戀愛(ài),甚至,連“人”的戀愛(ài)都不是。
它們都不是凡情,不需要去談。
它們更接近傳奇故事里的情,吃設(shè)定,并不需要太多的情感鋪墊。
設(shè)定告訴你,靈兒在仙靈島種石頭,等了逍遙哥哥很多年;段公子把王姑娘認(rèn)成了玉像,向來(lái)癡,從此醉;一位美麗少女住在開(kāi)滿(mǎn)茶花的山莊里,因?yàn)閻?ài)上表哥記了好多武功。
不需要細(xì)掰情之所起,故事就開(kāi)始了,他們就成親了,他們就愛(ài)了。
這也是一種成立的法則。
設(shè)定告訴你,這倆人是情天恨海,折淚還情,一句“猶如故人歸”不必再解釋ta為何特殊,幾乎每個(gè)聽(tīng)東方主義故事長(zhǎng)大的人,都能夠get這種浪漫。
這也是劉亦菲最擅長(zhǎng)的法則。
相反,一旦把她談情的脈搏拉長(zhǎng),細(xì)微到每次心跳,必然壞菜。
可《夢(mèng)華錄》偏偏反其道行之。
不僅創(chuàng)下劉亦菲談情最長(zhǎng)、最蜿蜒的曲線。在近年的古偶里,它也意外的“慢工出細(xì)活”,撒糖撒得夠細(xì),夠均勻。
不僅成立,還成立得幽微細(xì)膩、又欲望勾連。

說(shuō)白了,《夢(mèng)》很會(huì)拍情戲。
很少有人討論,情戲也需要有審美。
從兩處一窺:顧千帆和趙盼兒初初心動(dòng)時(shí),怎么表現(xiàn)的?
剛剛共歷了一段險(xiǎn)程,兩邊都暫得緩息的一個(gè)良夜。
顧千帆告別趙盼兒,坐船離開(kāi),繼續(xù)逃亡,盼兒倚樓而望。
月華燈影里,蟲(chóng)鳴水聲間。
男主想看又逃避,女主脈脈不得語(yǔ)。
只是畫(huà)面美,也算俗套。偏有一個(gè)劃船的手下,在男主耳邊嘰嘰喳喳。
妙的是,“視聽(tīng)”結(jié)合,此處用了一段淡出淡入的消音處理。
鏡頭一搖,遠(yuǎn)處的人影清晰,近處的話語(yǔ),卻低到聽(tīng)不見(jiàn);又一晃,近處的聲音在耳,遠(yuǎn)處的人,卻影綽難辨。

講動(dòng)心,卻不去講心。
心比耳朵笨,耳朵倒比心先誠(chéng)實(shí)了。只能捕捉自己在意的,硬灌都難聽(tīng)進(jìn)。
足夠有情人會(huì)心一笑的切實(shí)。
趙盼兒的心動(dòng)呢?
要到第十四集,男女主互救了幾波后。
閨蜜間扯閑片,被對(duì)方點(diǎn)破;你一去見(jiàn)顧千帆,臉上怎么就掛著笑模樣?
自己還不信,否認(rèn)。等人家把鏡子杵到眼前,自己照了,抵賴(lài)不得。

劉亦菲在這里的處理,也是可圈可點(diǎn)。
乍一看自己的臉,有陌生,有想藏笑、藏不住,還有些怔忡——
明明才被未婚夫甩了,意外于自己臉上已無(wú)愁色。
不能抵賴(lài),但開(kāi)口承認(rèn)得不甘,因?qū)Ψ降臅崦炼錅I。

很難想象,在與“仙氣”作戰(zhàn)多年后,我們反而從一部古偶劇里,看到了劉亦菲耽于凡情的可能性。
從這似乎玉石之軀上生芽出“我也似她”的情愛(ài)啟發(fā)。

天仙終于會(huì)思凡,便是下凡了么?
也不。
客觀來(lái)看,女主趙盼兒的各種設(shè)定,并不平凡。
首先是她的身份特殊,在所處群體中,境遇也絕無(wú)廣泛可能。
《夢(mèng)華錄》是以關(guān)漢卿創(chuàng)作的元雜劇《趙盼兒風(fēng)月救風(fēng)塵》為藍(lán)本改編的。
原故事中,趙盼兒是一位擅風(fēng)月、有手段、有肝膽的歌妓。
她的閨蜜宋引章,雖然也是個(gè)“狐魅人女妖精,纏郎君天魔祟”(盼兒調(diào)侃語(yǔ)),卻因?yàn)槟贻p不知事,不顧趙盼兒勸導(dǎo),在老實(shí)人安秀才和有錢(qián)、表現(xiàn)得作小伏低的商人周舍間,選擇嫁給了后者。
過(guò)門(mén)后,卻被周舍日日家暴,最后還是趙盼兒使出風(fēng)月手段,騙得周舍寫(xiě)了休書(shū),救她出了鬼門(mén)關(guān)。
以意志精神、個(gè)人魅力來(lái)講,原故事的趙盼兒也很不凡。
但她的身份是沒(méi)有太多前綴詞匯的,不是名妓,不是現(xiàn)代臆想粉飾后的花魁,她和她的姐妹,都只是底層歌妓。
她的結(jié)局(依然在風(fēng)塵打滾)也不會(huì)符合現(xiàn)代人寄望。

而《夢(mèng)華錄》將故事搬到宋朝,趙盼兒的設(shè)定改成了“賣(mài)藝不賣(mài)身”的樂(lè)伎。
出場(chǎng)時(shí),她已得太守恩令,脫離賤籍,成為齊民,經(jīng)營(yíng)著一家“趙氏茶坊”。
等待著她贊助過(guò)的情郎中榜,娶她做進(jìn)士娘子。
不難看出,女主基礎(chǔ)人設(shè)的塑造,比較其對(duì)應(yīng)群體,在每個(gè)階段里都充滿(mǎn)一種極端“幸運(yùn)”的設(shè)置。
比如,在做營(yíng)妓(伎,通妓,后者為前者的俗字)時(shí),得以落籍從良。
宋代的州郡太守對(duì)于營(yíng)妓的命運(yùn)有一票決定權(quán)(因營(yíng)妓作為官方商品,主要服務(wù)于州郡官、軍的公開(kāi)活動(dòng))《澠水燕談錄》曾記,有營(yíng)妓以年邁為由,向蘇軾請(qǐng)求脫籍——“公即判:從良任便。”
有相對(duì)幸運(yùn)的,自然也有不幸的。實(shí)際上,脫籍是很困難的事。
哪怕是像宋引章(林允 飾)——
劇中她的設(shè)定改為有名頭的樂(lè)伎,江南第一琵琶手。

蘇軾就曾以“色藝為一州之最”否了一個(gè)周姓名妓想落籍嫁人的請(qǐng)求。
誒,你的色藝雙絕,你不能走。
身份、境遇、狀態(tài)特定之外。
劇中盼兒的氣質(zhì)、思想、個(gè)性、技能、行為邏輯也都是很不凡的。
她聰明、氣質(zhì)出塵,無(wú)俗態(tài),思想獨(dú)立,上進(jìn),成熟又不失可愛(ài)。
無(wú)雌競(jìng)意愿、對(duì)同性有義氣。
而且,什么都會(huì)。
通詩(shī)曉畫(huà),茶百戲,蹴鞠,擲骰子……
三教九流通吃。

這仍是一個(gè)想象中的、被描補(bǔ)過(guò)的、集備現(xiàn)代美好寄托、理想化的女性人物。
當(dāng)然,無(wú)疑是與如今具有一定成熟感的劉亦菲適配的。
這也是《夢(mèng)華錄》的第二取巧之處:
人物有血肉感,有趣,稀釋了仙氣。
但,又并不在凡間。
而劇中出場(chǎng)的風(fēng)塵女子設(shè)定,其實(shí)也都不具有普適性。
是極端設(shè)定下的幸存偏差。
這些趙盼兒們,也框出了趙盼兒生活空間,搭建了“逐夢(mèng)互助”這一美好野望。


既不在天庭,也不在凡間,天仙到底被安排在哪了?
一個(gè)半真半假、恰到好處的、夢(mèng)華錄的異世界里。
導(dǎo)演為了構(gòu)建這個(gè)世界,確實(shí)是付出了很大誠(chéng)意。

實(shí)美人,實(shí)景,無(wú)愧東京夢(mèng)華。



但,也正因這半真半假,使它終究是有夢(mèng),有華,談不到“錄”。
何謂夢(mèng)華?
宋引章在東京街頭遇到花魁張好好,好好對(duì)她很友好,她開(kāi)導(dǎo)初來(lái)乍到,因出身而自卑的引章,說(shuō):
賤籍怎么了,平日里不愁吃喝、文人墨客們捧著、高官貴爵們敬著,既不用像平常的市妓賣(mài)身媚俗,整天穿金戴銀、呼奴攜婢,哪里不如那些升斗小民了。

如果說(shuō),“夢(mèng)華”體現(xiàn)于張好好的夸富。
比如,她所說(shuō)的高等官妓的優(yōu)渥的生活,確實(shí)為實(shí)。

那,沒(méi)有“錄”的,就是現(xiàn)實(shí)里官妓作為商品,作為士大夫們的炫耀性消費(fèi)。
她們的豪奢,本質(zhì)仍是被動(dòng)的,是典、借也必須維持的,是提高沽價(jià)的籌碼。
她們的個(gè)人財(cái)產(chǎn)其實(shí)是沒(méi)有概念也沒(méi)有保護(hù)的。社會(huì)普遍價(jià)值對(duì)于她們的財(cái)產(chǎn),也即所謂的“憑自己本事”賺來(lái)的錢(qián)的態(tài)度,是輕蔑的。甚至?xí)谐ⅰ⒐俑畮ь^巧立名目搶奪妓家財(cái)產(chǎn),如《翠微北征錄》就曾提及“強(qiáng)抑妓家交錢(qián)”之事。
張好好又說(shuō):
我們不是良民,但我們又賤在哪里呢?你有賣(mài)過(guò)身么?有為了錢(qián)財(cái)討好過(guò)男人么?以色事人才叫賤。我們靠自個(gè)兒本事吃飯,活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

這一段,這幾天在網(wǎng)上吵翻了天。
一方覺(jué)得,它將“妓女”分成了三六九等,美化古代女性苦難,且無(wú)視“以色事人”的妓女人群生存環(huán)境。
一方則覺(jué)得上綱上線,同時(shí)卻拿出所謂“史實(shí)”捍衛(wèi)劇中體現(xiàn)的設(shè)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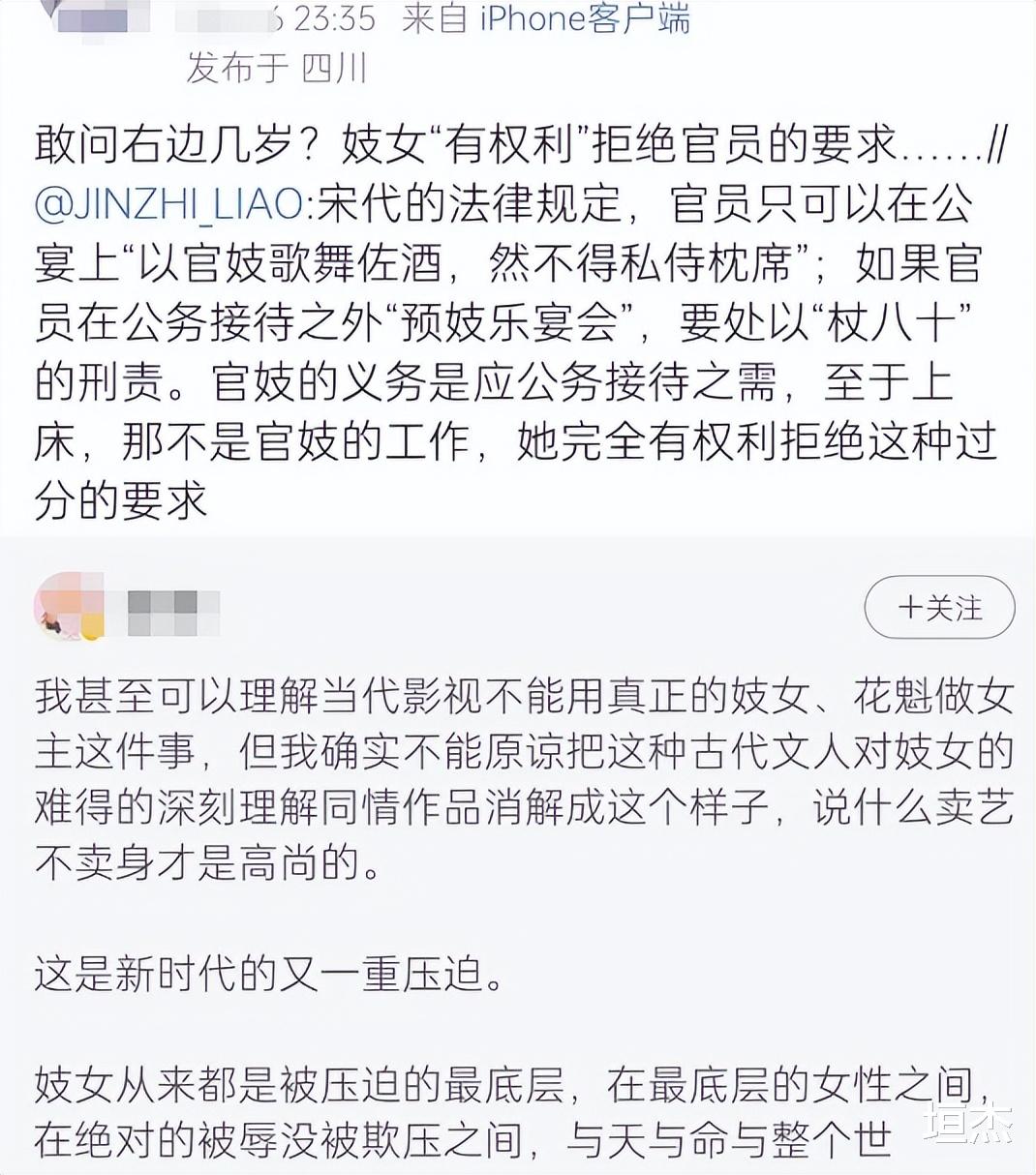

首先,伎不等于妓是一個(gè)偽概念,二者相通,但有所偏重。
這一點(diǎn)@于賡哲老師曾有詳細(xì)撥正過(guò),這里篇幅有限,不再贅述。
圖中“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它其實(shí)出自明中后期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馀》原文在接下來(lái)就講了一個(gè)知州與官妓私通,官妓被處死的故事。
而知州祖無(wú)擇進(jìn)了趟大牢又被保出來(lái)做官(宋史卷三三一記載,他是由于卷入王安石黨爭(zhēng)進(jìn)去的)而利用妓女打壓政敵是宋代文人一個(gè)常見(jiàn)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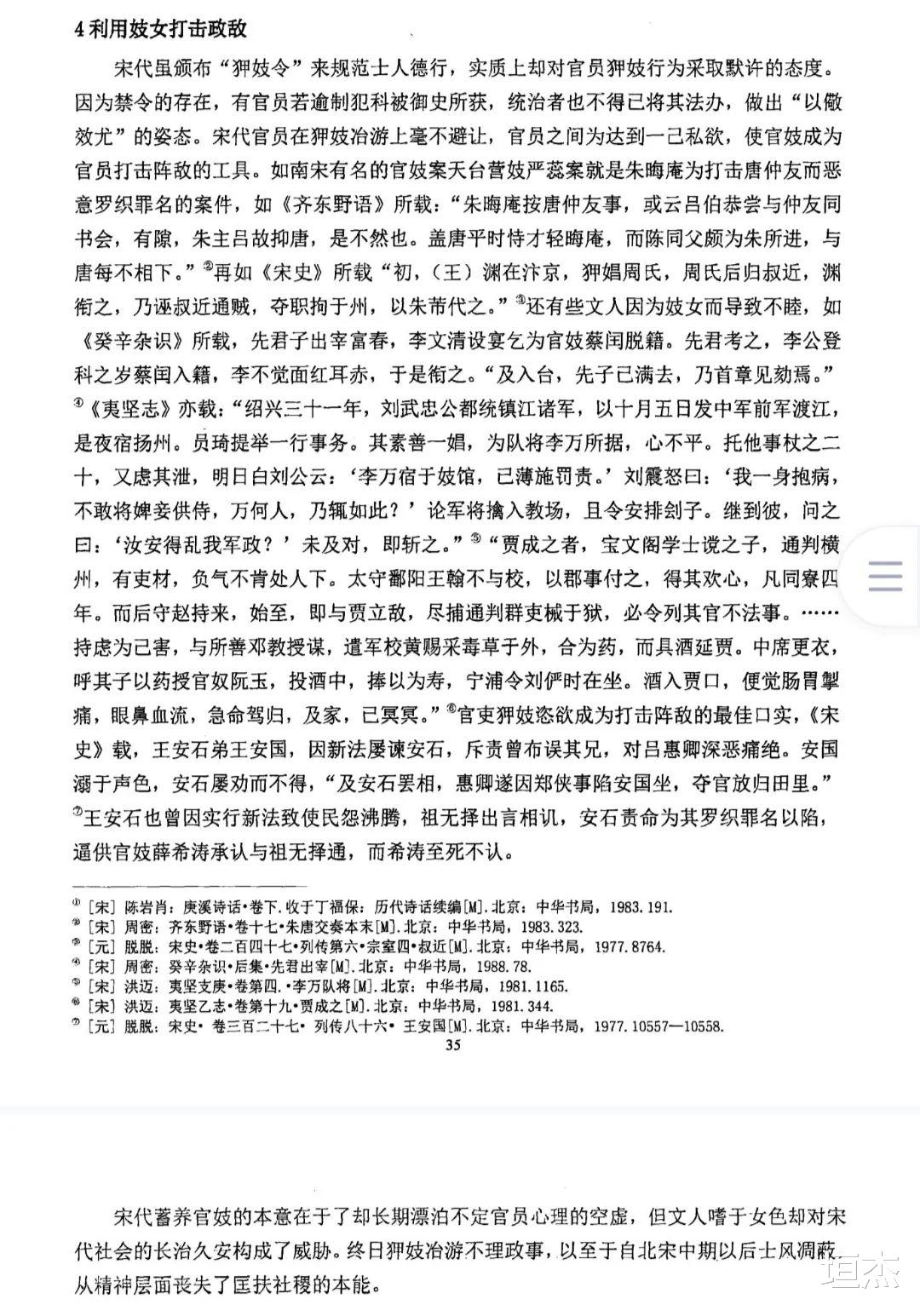
論文《宋代官妓研究》
其實(shí)這一類(lèi)評(píng)論者,大抵是沒(méi)有閱讀史料的習(xí)慣,及比較系統(tǒng)的史學(xué)認(rèn)知。
也很難歸類(lèi)于我們既已提出的哪種史觀持有人群。
他們或者只是看到了幾個(gè)詞條,援用作互聯(lián)網(wǎng)吵架的依憑。
實(shí)際上,宋代不僅有禁止,而且有一系列的禁止官員“狎妓令”。
然而,由于統(tǒng)治者的明禁暗縱、“上行下效,有法不執(zhí)”、“禁官員、但不禁學(xué)子文人”等等原因,致使其收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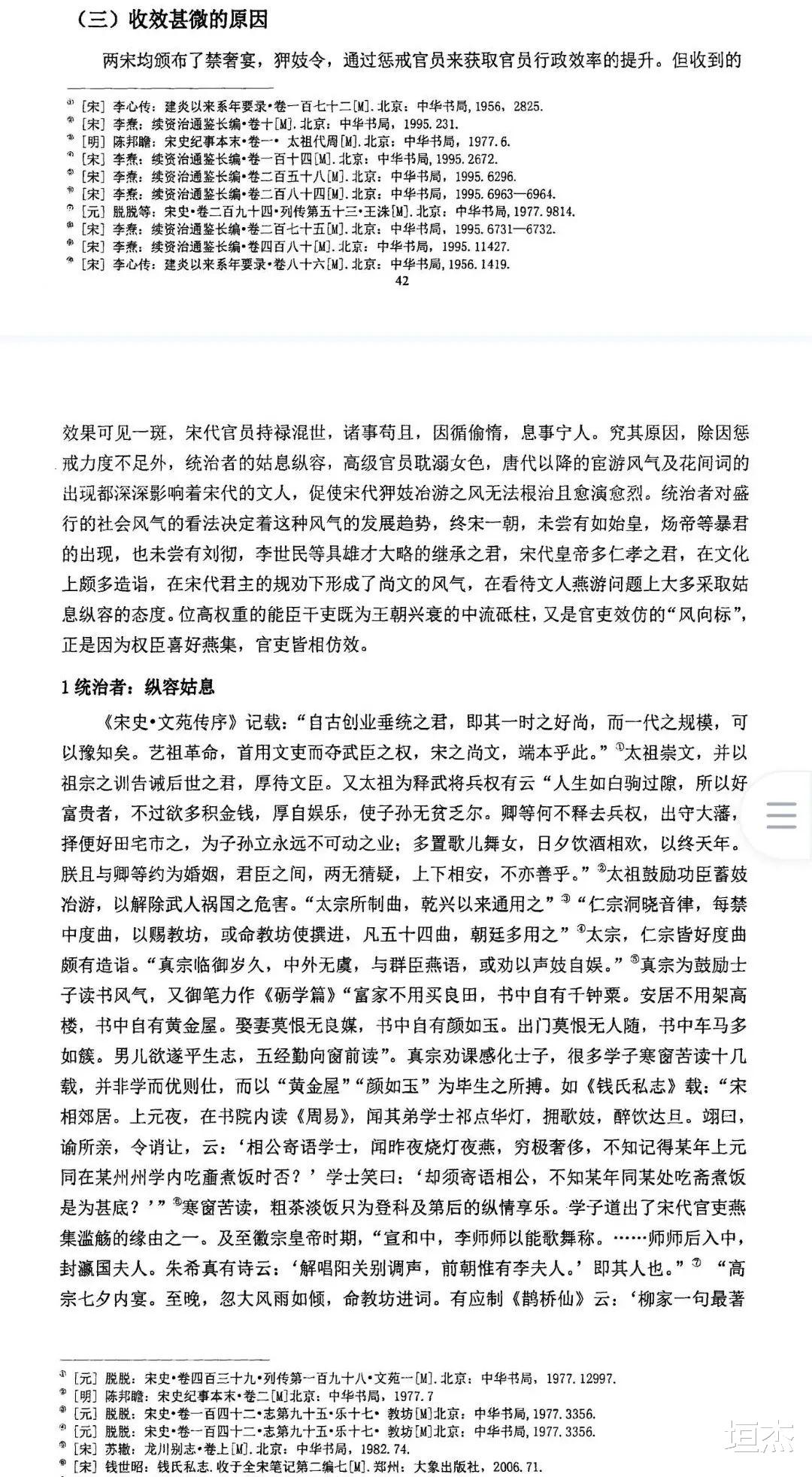
法條未必等于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普遍現(xiàn)象,這其實(shí)是非常常見(jiàn)的。
否則,僅看律條的“前衛(wèi)”,連《夢(mèng)華錄》的基本矛盾設(shè)置也可以推翻。
比如劇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良賤有別”,在學(xué)界就一直有關(guān)于“宋時(shí)良賤制度的消亡”的研究,這是因?yàn)樵谒未小芭局贫雀臑楣蛡蛑贫取钡南嚓P(guān)推法。
但其實(shí),民間公案里依然大量存在“良賤之別”,僅有一些奴婢即使轉(zhuǎn)雇傭制,而對(duì)雇傭奴婢的管理依然與良民有很大不同。何況,尚有大量的奴婢沒(méi)有轉(zhuǎn)制。他們依然是主人的畜產(chǎn),“不得稱(chēng)人”。
一切有涉賤籍的條例,其實(shí)都可以看其是為了保障誰(shuí)的利益。
而至于“可以不賣(mài)”、“有說(shuō)不的權(quán)利,你不說(shuō)”,其實(shí)也反映出沒(méi)有比較成熟的社會(huì)觀。這里篇幅有限,如果我明天可以對(duì)老板的加班要求有權(quán)說(shuō)不,我們?cè)賮?lái)討論彼時(shí)的賤籍人權(quán)問(wèn)題。
問(wèn)題也有是否值得討論之別,而《夢(mèng)華錄》能引起這樣廣泛的討論,已見(jiàn)得它是有觸及到什么的。
作為一部古偶,到這里,其實(shí)已經(jīng)完成使命了。
而它衍生的問(wèn)題,其實(shí)在當(dāng)下并不罕見(jiàn)、甚至是飄也常審視自己規(guī)避的。
即是,當(dāng)我們展現(xiàn)、關(guān)懷一個(gè)弱勢(shì)群體時(shí),我們所聚焦的,不能夠是特例。
因?yàn)楫?dāng)我們所舉例為特例時(shí),即使是無(wú)意的,無(wú)形中,已經(jīng)會(huì)拔高基本標(biāo)準(zhǔn)。
我舉個(gè)可能需要想兩道,但如果想明白,就一定能聽(tīng)懂的例子:
比如,我們探討女性生育話題時(shí),以一位各方面都很優(yōu)秀,成功,在道德與情操層面也非常完美,甚至是對(duì)社會(huì)有相當(dāng)程度貢獻(xiàn)的女性舉例。
那結(jié)果,一定是失實(shí)且不嚴(yán)肅的。
而這兩點(diǎn),顯然已與“古偶”的本質(zhì)打架。
輕拿曉夢(mèng),沉放青史。
各有各的門(mén)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