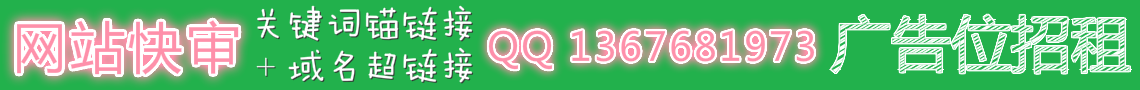比起男性角色來說,歐容似乎對女性角色和女演員更為迷戀。
影片《沙之下》、《八美圖》、《游泳池》、《天使》、《傀儡》、《花容月貌》、《雙面情人》都是以女性角色為中心的。
歐容還表現出對于老年女演員的熱愛,比如《時光駐留》中的讓娜·莫羅以及《雙面情人》中的杰奎琳·比塞特等。這些優秀女演員的加入讓歐容的影片星光熠熠,這也成為他與主流相融合的重要推動力。

在談及為什么喜歡拍攝女性時,歐容曾說道:
“因為我是如此不同,所以我更有能力看到她們的本來面目,也因為她們的不同,我能更好地認同她們。我喜歡把自己定義為女人,盡管我不是”。
身份認同在歐容這里可以跨越性別界限,而這種差異恰巧是促成認同的原因。
厭女的指責
厭女文學是男性敵意的主要載體。
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提到了兩個厭女癥的經典神話,分別是潘多拉的傳說和《圣經》中人類墮落的故事。潘多拉的故事顯示男權制的宗教和道德將因欲望引發的危險和邪惡完全歸罪于女性。

《圣經》中人類墮落的神話依然以女性為人類苦難、知識和罪惡的根源。以至于女人、性和原罪被聯系在一起,成為西方男權制思想的基本模式。盡管歐容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對女性的喜愛,但他也經常受到厭女的指責。
短片《胃里的手指》講述了一個患有暴食癥的女人在暴飲暴食后自我嘔吐的過程,公共聚餐的精神在這里被扭曲了。《夏日父母》是一部由歐容父母主演的短片。短片中,夫妻二人到山上徒步旅行,安娜·瑪麗站在丈夫的身后,試圖把他推下懸崖。

盡管安娜抵制住了殺人的誘惑,但歐容并沒有停止他對謀殺的迷戀。
女性謀殺的主題接連出現在《看海》、《失魂家族》、《八美圖》、《游泳池》等多部影片之中,除去《看海》是對女性的謀殺之外,其余影片均表現了女性對男性的謀殺。《失魂家族》中,女兒蘇菲將老鼠/父親殺死,家庭秩序得以重建。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中提出了“卑賤”的概念,并把卑賤定義為“藐視邊界、位置、規則”,是那種“擾亂身份、系統、秩序者”,是“意義崩潰的場域”,克里斯蒂娃把卑賤的形式分為三類,分別與食物、廢棄物和性差異相關。

它與陰性的等同與父系象征態相對,既是嫌惡也是欲望的焦點。或許我們可以借用卑賤的概念來探討歐容早期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影片《看海》中的塔蒂亞娜是卑賤的所指,而她本身也與食物和廢棄物相關聯。
當薩沙第一次邀請塔蒂亞娜吃飯時,她不僅狼吞虎咽還十分不雅地用嘴巴舔干凈盤子。而當莎莎第二次和他分享早餐時,塔蒂亞娜卻在超市里看著生肉,此時的背景音樂卻是塞薩爾·弗蘭克(césarFrank)的《PanisAngelicus》(中文譯為《天使之糧》),無疑是對陳列生肉的諷刺。

聲畫對立的使用增加了觀眾對于塔蒂亞娜的厭惡,塔蒂亞娜在薩沙家的浴室洗澡時,把薩沙的牙刷與未沖洗的糞便混合在一起,這種行為混合了干凈與骯臟,也使身體的兩端和消化過程結合在一起。
它們之所以特別強大,是因為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破壞了身份的穩定性。
影片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排泄物,而且把它與母親的身份相關聯。塔蒂亞娜在與薩沙討論生產的問題時,詢問薩沙在生產時有沒有排泄物,有沒有進行排便。
批判的凝視

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將男女差異的討論作為中心問題,認為在精神分析的菲勒斯中心主義之下,女人是作為缺乏或被閹割的形態進入符號系統的。是反映欲望的他者。在象征秩序的限制里,男人可以通過語言命令把自己的幻想和迷戀強加給沉默的女性形象。
而女人作為被看者出現,不斷地被塑造成男性的客體。主流電影把色情符碼編入了占主導地位的父權秩序的語言之中。在分析視覺快感的機制時,穆爾維將之分為兩個方面,分別是窺淫性質的快感和自戀性質的快感,試圖表明這兩種形式的快感機制在歐容的作品當中都是不成立的。

傳統上被展示的女人在兩個層面上起作用:作為銀幕故事中人物的色情對象以及作為觀眾的色情對象。
主流電影往往將觀眾的凝視與影片中男性角色的凝視結合起來,但歐容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穆爾維所批判的缺乏主體性的女性天使,她們或是上一節所提到的帶有危險性的殺人兇手,或者是擁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精神問題,亦或者是具有各種各樣的越軌行為。

但歐容電影中并不存在可以作為男性觀眾“理想自我”的男性英雄來強化他的身份感。并且如前所述,在《八美圖》等影片中,男性往往是缺席的。
《游泳池》中男性角色對女性角色的凝視來自于女性的主動。薩沙為了不讓馬塞爾發現弗蘭克的尸體用身體引誘了馬塞爾,傳統意義上的男性主動與女性被動的二元劃分在這里被解構。

而在《八美圖》中,施虐的對象似乎變成了男性,馬塞爾的死引發了八個女人對死亡真相的調查,而隨著調查的展開,馬塞爾的神秘面紗也被揭開。
作為父權制的大家長,馬塞爾與亂倫等越軌的行為相關聯,影片最終也讓他受到了死亡的懲罰。歐容賦予了她的女性角色擁有和運用凝視的權利,而不僅僅是凝視的對象。
這在影片《八美圖》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八美圖》中的每個女人都有一段屬于自己的歌舞表演,以揭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這與傳統的女演員在電影中的表演有所不同,沒有唱歌的女性角色會以觀眾的身份出現在鏡頭前,這加劇了電影中的酷兒張力。

值得注意的是皮埃萊特的表演片段,在這個片段當中,環境中的燈光變暗,聚光燈對準了她,其他的女人也都自在地坐下來看著她的表演,香奈兒則在她的表演過后熱情地鼓起了掌。第四堵墻在這個片段當中被打破了,因為演員是對著攝影機進行表演的,攝影機的闖入加劇了觀眾的間離意識。
虛構戲劇的現實感和真實感消失了,觀眾的認同被弱化。因此,女權主義的觀眾或許能在這部影片中占據一個更舒適的觀看位置,因為她知道屏幕上的這些女性可以盯著觀眾看,因為她們也是彼此的觀眾。

女性的凝視同樣出現在奧古斯汀變裝這場戲中,她化了妝,摘下了眼鏡,穿上了姐姐的禮服,瞬間有一個脾氣古怪,容貌丑陋的老女人變成了一個和麗塔·海華絲相似的人,正如瑪麗·安·多恩在談到貝蒂·戴維斯在《揚帆》中的形象時所說:
戴眼鏡的女性既象征著知性,也象征著不受歡迎,但當她摘下眼鏡的那一刻,她就變成了一個奇觀,一副欲望的圖畫。
面對這幅“圖畫”,其他人紛紛投來了贊賞的表情,好像之前的羈絆不復存在一樣,奧古斯汀雖然表面上希望吸引男人,但實際上她更渴望得到其他女人的尊重。她的蛻變讓觀眾和奧古斯汀的家人感受到了一種坎普式的快樂。
身體書寫

電影《八美圖》中呈現了三組曖昧的女性關系:加比與皮埃萊特;加比與露易絲;皮埃萊特與香奈爾。
值得一提的是加比與皮埃萊特接吻的一場戲,加比在完成了自己的音樂表演后,皮埃萊特與她展開了關于男人的討論,此時的人物調度與《干柴烈火》中的片段相類似,皮埃萊特一邊闡述她對男人的失望,一邊圍繞著加比轉圈,就像在引誘自己的獵物。
在表達了對加比的信任之后,二人倚靠在窗邊,門框在此將二人的身體隔開,預示著二人接下來的矛盾:她們擁有共同的情人。為此兩人大打出手,但經過一番打斗之后,一個漫長的,充滿激情的吻隨之而來。

這個出人意料地吻化解了二人之間的矛盾。
如果女人在對男人的愛里感覺不幸福,在以后的歲月里,暗流將被力比多再度啟動,并且視情況有不同程度的強化。加比的情人背叛了她與皮埃萊特上床,后者給了這個男人一大筆錢,而他卻帶著錢逃到了墨西哥。

《游泳池》中對朱莉和薩拉之間的同性感情展現的較為含蓄,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三個相似鏡頭的疊加中看出端倪。
第一個場景中,朱莉穿著一身白色泳衣躺在泳池旁,鏡頭親密地觀察著她性感的身體曲線,隨后鏡頭上搖,露出了弗蘭克的身體。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這是薩拉的幻象,尤其是這一場景夾雜在兩個薩拉睡覺的場景之間。
第二個場景中,薩拉穿著泳衣躺在了幾乎和朱莉一樣的位置上,鏡頭調度也是從右至左然后上搖,我們發現馬塞爾站在她旁邊,與第一個場景中弗蘭克站在朱莉旁邊如出一轍,隨后鏡頭切到薩拉在水中的倒影,流動的波紋提醒我們這是薩拉的幻象。

隨后她便被跳入泳池的朱莉吵醒,結束了這場白日夢。
緊接著下一個鏡頭中朱莉躺在泳池邊,她邀請朱莉共進晚餐。
三個鏡頭的疊加凸顯了薩拉與朱莉之間曖昧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