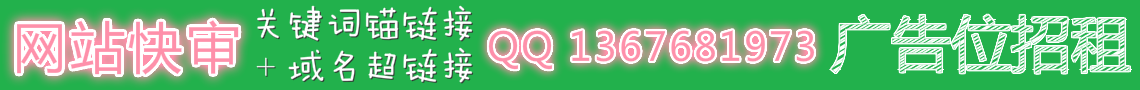吳宇森是第一個被好萊塢電影公司聘用的香港導演。當時的美國電影公司對《喋血雙雄》等一系列經典港味電影的動作執導印象深刻,為此促成了吳宇森的旅美之路,并于1993年憑借《終極標靶》首次亮相好萊塢。

當時他與好萊塢的關系并非十分融洽,因為制片公司對他的拍攝想法干涉得太多,他覺得自己無法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拍出一部電影。1997年,當他在香港為他的第三部好萊塢電影《變臉》的上映做宣傳時,他接受了某記者的采訪,總結如下:
你是如何規劃一個動作場景的?
我從不使用分鏡,我都在腦海里演繹,有許多動作場景是我在片場中才想到的。為了獲得靈感,我通常會根據故事中發生的事情和地點來構思,對拍攝現場發生的任何微小細節都非常敏感。如果我看到任何可以融入動作的元素,當下就會去使用它。
聽說你在執導的時候喜歡聽音樂?
我傾向于通過動作畫面去感受電影,所以音樂很重要。在《終極標靶》的咖啡館場景中,尚格·云頓在咖啡館外與四個人打架的慢鏡頭想法就來自于聽爵士樂,我想在那一幕中表現出一種憂郁的爵士樂的感覺。

你會經常切換播放的音樂嗎?
這都是憑直覺。在激烈的動作場景中我會放搖滾樂;在氛圍輕快的場景中我喜歡聽爵士樂;如果拍攝的是大型的動作場景,我更喜歡聽古典音樂,比如瓦格納。
聽說你引用過漫畫里的打斗場景?
我小的時候對漫畫很著迷,還有約翰·福特、約翰·韋恩、霍華德·霍克斯等導演拍的美國西部電影,我都看過。我也受到了美國音樂劇的影響,我喜歡吉恩·凱利、弗雷德·阿斯泰爾、《雨中曲》、《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和《西區故事》。
當我拍攝動作場景時,我會想到音樂劇,我傾向于像拍攝舞蹈場景一樣拍攝它們。當數百人在鏡頭前打架時,就像很多人在舞臺上跳舞一樣。

有多少動作場景是在剪輯室完成的,需要拍很多鏡頭嗎?
是的,需要拍很多鏡頭。因為我總是親自剪輯,所以當我拍攝畫面時,我總是在思考我該如何剪輯它們。通常需要用三到四個攝像機,如果是一個較大的動作場景,可能會用六到七個攝像機。
在好萊塢拍電影有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嗎?
有的,當我拍攝《終極標靶》時,我必須提前為它制作分鏡,以往我都是不這么做的。在好萊塢拍電影,我必須先構思我的畫面,這樣公司才能計算出預算。

描寫暴力場景吸引你的是什么?在這方面,你是否受到了薩姆·佩金帕等人的影響?
前面提到我小的時候看了很多西部片和黑幫片,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的電影。包括讓-皮埃爾·梅爾維爾的《獨行殺手》,還有薩姆·佩金帕的《日落黃沙》等美國導演的電影。
佩金帕對慢鏡頭的運用和對浪漫主義的強調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成功地喚起了一種美好的感覺。
你在童年時期遭遇過很多暴力事件嗎?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非常的混亂,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家里很窮,家里有七年的時間居無定所,和各種社會分子生活在一個混亂的片區里。我參加過幫派斗毆,打過別人,有時也被人打。但不得不說,我有很好的父母,我們一家是路德教徒,他們教我要有尊嚴地生活,要遵守教會的規矩。

你認為電影中的暴力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嗎?
我討厭現實生活中的暴力。有時我看新聞的時候,看到有人毆打,有人被殺了,就會不自覺地哭出來。我討厭那樣的社會,太難受了。但在我電影里的英雄不同,他們用強大的力量去抗爭暴力,這也是我喜歡拍動作片的原因。
作為傳奇導演張徹的助理導演,他是否影響了你對電影中暴力的看法?
當然,他強調了男性之間的紐帶,或者“兄弟情誼”的概念。我們的英雄們在為正義而戰,他們有時需要在與暴力的斗爭中自我犧牲,就像古代的中國俠士一樣。但在現實生活中,用暴力對抗暴力是不好的。
此外,動作和暴力也不是我電影里唯一的東西。我喜歡展示人性中好的一面,包括忠誠、榮譽、尊嚴和騎士精神等。有些東西現在已經丟失了,我之所以喜歡談論它,是試圖把它找回來。

你會繼續在好萊塢拍更多的電影嗎?
好萊塢很棒,我在這里學到了很多經驗,但我還是打算回香港,因為香港是我的家,我想念那里的人和物。
如果有機會,我想在香港把好萊塢和香港的技術融合起來拍一部像《三國演義》那樣的宏大作品。我的夢想是拍一部像大衛·里恩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或黑澤明的《亂》那樣的電影。(在2008年和2009年,吳宇森也終于如愿地拍出了《赤壁》這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