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不小心就成了脫口秀新星—
「法國作家和中國作家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如果你是個文學大師,被問到這個問題時,第一反應會是什么?
反正如果是我,大概率會絞盡腦汁從兩國文化、生活方式的異同來全方位分析,恨不得發表一篇論文以彰顯——我是個文化人。
然而,真正的文學大師余華卻語出驚人,回答說:
「最大的區別就是法國作家用法語寫作,中國作家用中文寫作。」

這……雖然差點意思,但也不能說不對,而且還頗有點四兩撥千斤的意味。
余華能有什么壞心眼呢?
只是喜歡直抒胸臆罷了。
這當然不是余華第一次在公眾面前淪為「笑料」。
有人打聽《活著》的版稅收入,余華說:「我靠《活著》活著」。

有人問他,滿分10分的話,給《活著》打幾分?
他回答:「9.4吧,那0.6扣在哪?問豆瓣去吧」。

去年他上《朗讀者》,多有文化深度的一檔欄目啊,余華和主持人聊闌尾聊得繪聲繪色。
他說,小時候自己和哥哥因為不想上學,就耍賴說肚子疼。
誰成想當外科醫生的父親是個實干派,直接就把兩人的闌尾給割了。
于是乎,余華一家人的闌尾都是沒有了的。

幽默永遠是最后的贏家。
當闌尾出場,瞬間所有話題就都「后宮粉黛無顏色」。
而余華與闌尾的淵源,這還不算完。
1994年,余華創作了一篇短篇小說,名字就叫《闌尾》。
故事由第一人稱「我」展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兩兄弟的父親是一個外科大夫,經常做作闌尾手術。他還給兩兄弟講了一個英國男人自己給自己割闌尾的故事。
于是,「父親給自己做手術」的念頭便深深植根于兩兄弟。
后來,竟終于給他們逮到機會——父親在家時得了闌尾炎。
兩兄弟沒有按照父親的指示去叫醫生,而是讓父親自己給自己做。
最后,父親因為二人的拖延耽誤了病情,從此再也不能做手術了。
結尾余華還不忘點題。
父親對妻子說:
「你給我生了兩個兒子,其實是生了兩條闌尾,平日里一點用都沒有,到了緊要關頭害得我差點丟了命。」
余華的幽默特質,早在那時就初顯端倪。
只是直到2021年的末尾,才終于被看到。

從牙醫到作家,主要是為了閑晃—
余華說自己「認識的漢字不多」,所以《活著》只有12萬字。
這話可能是真的。
他說自己當作家就是為了能睡懶覺和不上班。
也不假。

余華出生于醫生之家,父親是外科醫生,母親是護士長,家就住在離醫院不遠的地方。
恢復高考以后,17歲余華報考,落榜,第二年再考,再次落榜。
一個還不到20歲的人,讀不了書,該做些什么呢?
父母于是動用自己的關系,安排余華去做了一名牙醫。
就我們現在來看的暴利行業,對余華來說卻是個苦差事。
每天他要面對的是口腔、舌頭、口水……算不上是什么舒適的體驗。
工作本身也沒有什么創造性,只是無意義的重復,日復一日的經驗,只能讓人成為熟練的拔牙工人罷了。
而與之相對的,縣文化館里的人似乎格外自在的樣子,每天就在街上溜達,好像什么也不用做似的。
當了5年牙醫,拔了大約1萬顆牙齒后,余華受夠了,「我一天拔8個小時的牙,你們在大街上東逛逛西晃晃」。

打不過就加入,余華琢磨著棄醫從文。
很快,他憑借著天賦和努力,進了文化館,還因此寫出了「躺平文學」的上乘之作——
「第一天上班時,特意晚到了半小時,發現我是第一個到的,我就知道,我來對地方了。」
細看他的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還有近幾年新出的《文城》,個個都書寫的是時代洪流下的小人物,通常都有著悲慘的、跌宕起伏的命運。

<《活著》劇照>
有人說,很難想象一個能寫出無窮悲慘命運的作家,私下里竟然如此幽默。
我卻覺得,兩者是相得益彰的。
作家的寫作,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消耗自我,創作過程中如果不投入足夠多的心力和感情,是寫不出好作品的。
也因此,才會有很多人將作品戲稱為「我的孩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如果與自己的作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作品題材過于厚重的情況下,是會承接不住的。
而個人的輕巧與幽默,恰恰可以幫助余華與作品保持距離,這也讓他的創作更加不受限。
余華不一樣的地方,正在于他的這份漫不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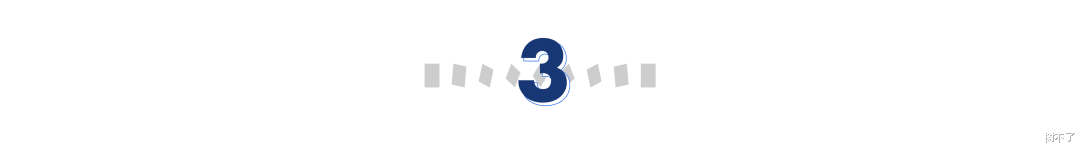
反矯情達人,非他莫屬—
余華到魯迅文學院進修期間,和莫言住一個宿舍。
他評價余華說:「他說話期期艾艾,雙目長放精光,不會順人情說好話,尤其不會崇拜‘名流’。」
可以,這很余華。
文字簡練是因為沒文化;當作家是為了偷懶。
親手把每一個試圖扣在自己頭上的高帽子摘下來的余華,可謂是當代反矯情大師。
前面已經提到,余華童年時生活在醫院附近。
也因此,他很早就對血和死亡習以為常。
當你習慣于看見渾身是血的醫生父親從手術室走出,當你不得不伴著太平間的哭聲入睡時,一個人自然很難再對其他事情感到大驚小怪。

他甚至給自己開發了新的樂趣,在炎熱的夏天跑去太平間睡午覺,因為——「那個地方特別涼快」。
對死亡都司空見慣的人,當然是做作不起來的。
這就是余華的魅力所在。
作品苦大仇深,本人憨態可掬的作家,不止余華一個。
他讓人過目不忘,全都因為真實。
由著名導演賈樟柯執導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受訪者有很多文學大家,氛圍也是比較嚴肅的。

一到余華,瞬間好笑起來。
連導演本人也說,余華就像個脫口秀明星。
有人說,他憑一己之力讓這部紀錄片好看了起來。
可能是只有他的言語間處處在表露,我是個「人」。
在其他作家還在探討寫作對自己而言的意義時,余華用滿是戲謔的語氣聊退稿。
提到改稿,也一點不苦大仇深,聲稱「只要能發表,我可以從頭光明到尾」。

看著眉飛色舞的樣子,簡直像個「小市民」。
當然,「小市民」也有細膩敏感甚至詩意的一面。
他講自己收到別人的書信,小心翼翼打開,生怕折碎了,錯過了對方的心意。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部紀錄片的題目其實源起余華。
在采訪中,他說,自己當年在海中游泳,希望可以游出渾濁的黃色海水范圍,一直游到藍色海水當中的故事。
導演賈樟柯當即就表示,想用「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當作片名,余華也欣然答應了。
幽默,但不淺薄。
也無外乎余華快速打入脫口秀界,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