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退賽。”
“樂壇沒有什么進步。”
一曲過后,信在臺上道出心聲。

鏡頭閃到臺下。
呆滯。

錯愕。

不解。

頃刻之間,氣氛詭譎。
場面一度陷入慌亂。
發生了什么?
鏡頭回到某綜藝。
信與康姆士樂隊,合作一曲《玫瑰竊賊》。
為達成契合,信更弦易轍。
卸下冷酷臉,收起嘶吼嗓。
一改唱腔,柔情款款,好似行云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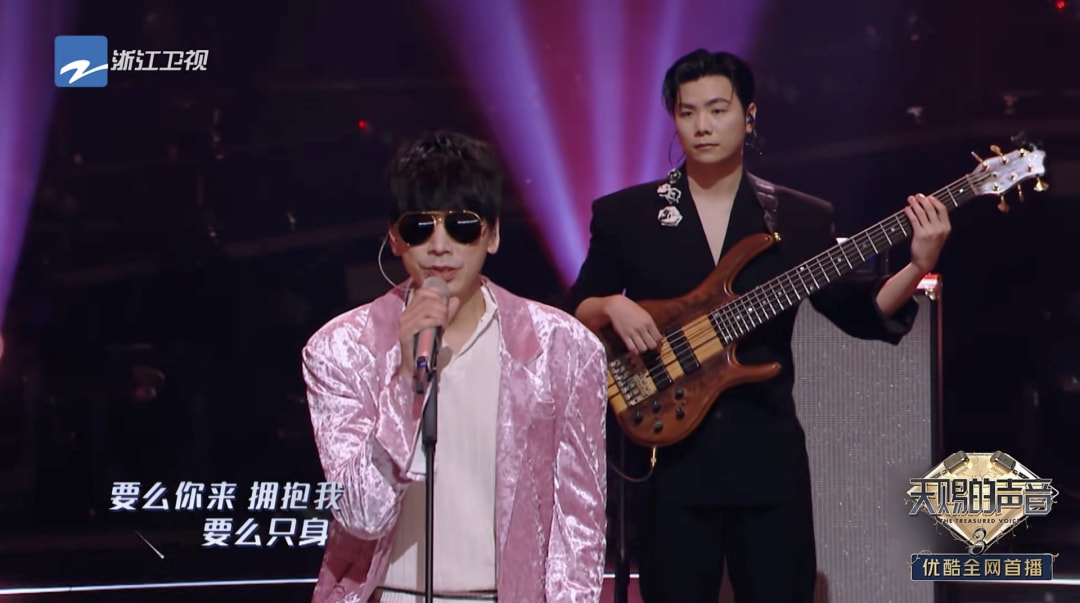
表演結束,稱贊聲此起彼伏。
周深驚嘆:“感受到了信哥的溫柔。”

面對褒獎,信舒眉展眼。
1米9的大高個,竟笑中含羞。

突然,一通發言,打破和諧。
采訪環節。
康姆士樂隊主唱表示,從組樂隊起,他一直在做原創,而翻唱是種挑戰。
不知怎的,“翻唱”一詞,點中了信。
他猛地跳出來,拋出靈魂拷問。
對準節目組——
“所有的電視臺都在搞翻唱,你要叫我們怎么進步?”

質問音樂人——
“只有編曲在進步,只有唱功在進步,那我們的原創在哪里?”

朝行業開火——
“唱翻唱的意義在哪里?”

直往脊梁骨戳。
面對此番詰問,現場刀光劍影。
主持人、音樂人、樂評人,皆站在節目角度打圓場——
音綜生存不易。
原創門檻太高。
至少還在玩音樂。

見得不到答案,信不再追問。
以退賽結束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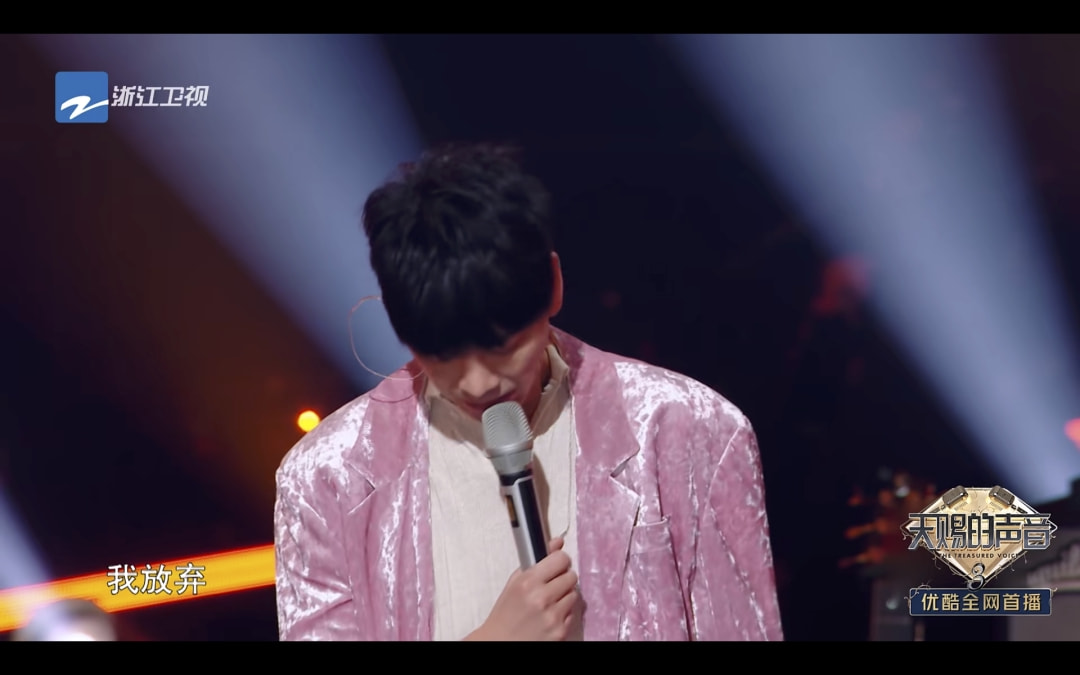
爭議卻沒有隨之停歇。
眾人納悶。
一開口,撕下樂壇遮羞布。
一番話,得罪半個娛樂圈。
他怎么敢的?

信的性格,很軸。
正向的“軸”,是孜孜不輟。
負向的“軸”,是固執拘泥。
而大眾對信的評價,卡在中間,占比五五開。
真人秀節目,講究一個“真”。
人設。
情商。
微表情。
通通離不開鏡頭審視。
稍有不慎,聲名狼藉。
信不以為然。
同一節目,兩次發飆。
隨《花樣男團》節目組,開啟東歐之旅。
身處異國,多有不便。
出行、語言、消費,舉步維艱。
面對挑戰,信毫無怨言。
一次任務,信和賈乃亮搭檔,需要在咖啡館完成點單。
二人興致勃勃,疾步前往。

到了咖啡館,還沒來得及坐下。
服務員以眼神,上下打量一行人。
信從中讀取出輕蔑、歧視、反感,徹底被惹怒。
他破門而出。
嘴里嘟嚷著:“我死都不喝!”
工作人員提醒。
“任務還沒完成。”
“不喝。沒什么了不起的。”
邊走邊罵,后期“嗶”聲無數。
一旁的賈乃亮,趕忙拽住信,生怕他做出破格之舉。

半道離場,任務自然前功盡棄。
信了無懼色。
他只納悶:“同為人類,憑什么你看我們的眼神,是如此不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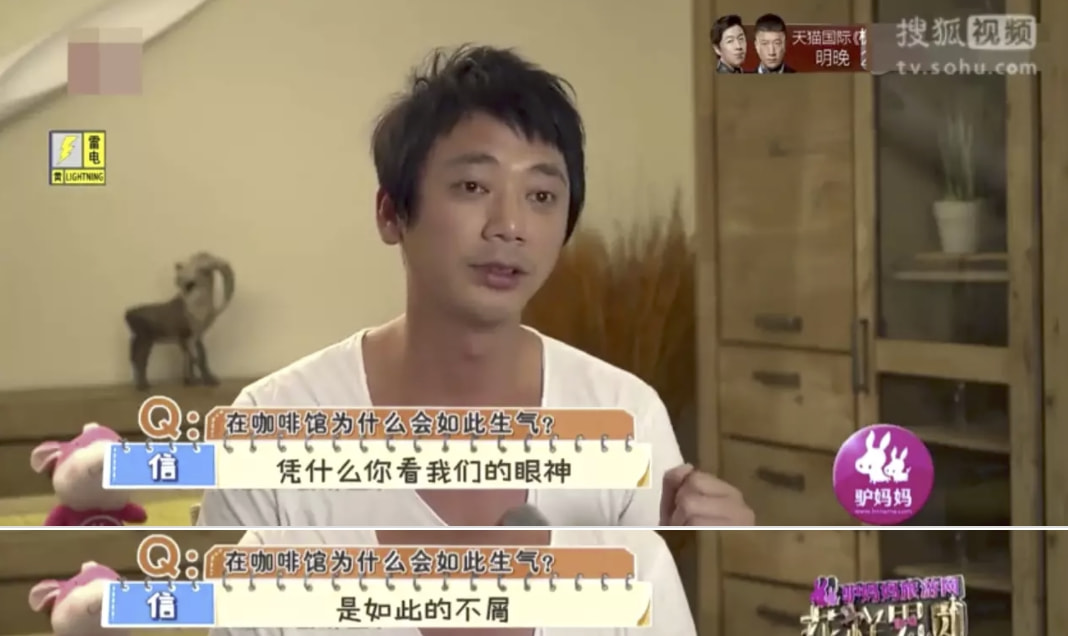
面對不公,他激烈反抗。
全然不顧鏡頭背后,一雙雙審視的眼睛。
娛樂圈個個人精,早已練就一套生存法則。
深諳為人處世之道。
通曉審時度勢之理。
在真人秀里,圓滑周全,露才揚己。
信滿不在乎,他要的是盡興。
參加節目前,導演問他,何為真人秀?
信答,出其不意,任情恣意。
導演很滿意,對他說:“要盡量的出其不意,盡量的放松做自己。”

難得有節目這樣要求,信覺得很有意思,便答應了下來。
于是,在節目中屢屢放飛自我。
酒足飯飽,快意當前。
節目組的任務,悄然而至。

見同伴們哭喪著臉,信靈光一閃。
“要不我們逃跑吧。”

郭德綱也被這新意吸引。
酒精作祟之下,一幫人上演了“男團出逃記”。
把這段經歷稱為:第一次真正的真人秀。

叛逆出逃,遺患無窮。
執行導演找不著人,急出了眼淚。

節目原本的進程,也被迫停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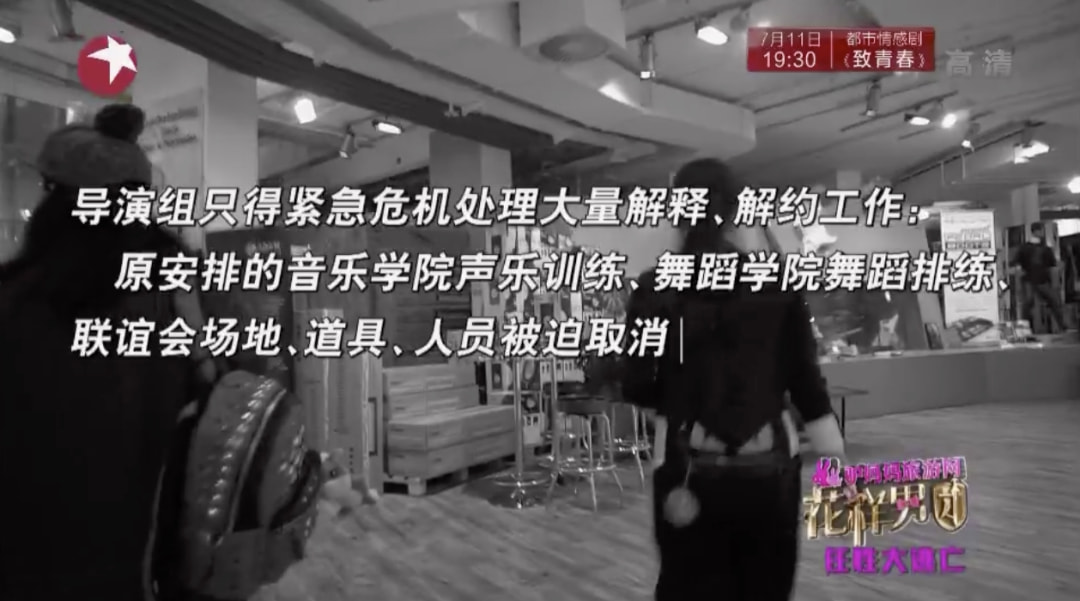
事情敗露后,節目組喊來一幫人:燈光、攝影、執行、導演。
花樣男團,四面楚歌。
見此情景信很不解。
做錯事,可以協商,可以罵,可以罰。
“弄那么多機器來拍,是要怎樣?”

導演組不依不饒,直言損失嚴重。
信丟下一句:“我賠。”
而后怒摔椅子,憤然離席。

一聲怒吼,滿座皆驚。
導演組嚇得夠嗆,不敢再大聲叫嚷。
與此同時,信意識到此前出逃的錯誤,誠懇致歉。
但他也疑惑。
“你們不是一直要真人秀嗎?”

信認死理。
縱使利害切身,仍學不會昧己瞞心。
如此一來,利弊兼具。
你如果欣賞,他就是堅持原則。
你如果反對,他則是死心眼兒。
信是一個與時代脫節的人。
或者說,是他主動與外界隔絕。
有段時間,信經常丟手機。
他心一橫,干脆停用。

絲毫沒有想過,不用手機會有什么后果。
公司找不到信。
只能提前排好通告,等他一個禮拜來確認一次。

朋友約他吃飯。
要么口耳相傳,要么提前三天聯系。
因為信工作忙,回家才有空查看郵件。
地點一旦有變化,必須有人在老地方等他,否則他找不到地兒。

即使是女兒,也只能在家里找到他。

親近之人,尚且如此。
外界如何與信取得聯系呢?
一個字:蹲。
信的社會關系簡單,往往是公司和家,兩點一線。
通訊工具單一,社交全靠電子郵件。
找到信的途徑,要么線下蹲,要么線上蹲。
久而久之,他成了李誕口中“娛樂圈最難找的藝人”。

身處21世紀,實在無法想象沒有手機的日子。
有人曾問信,為何不用手機?
信做出解釋。
一來,天底下沒有太多,一定要關注的事。
二來,他不認為自己有多重要,需要到全世界都在找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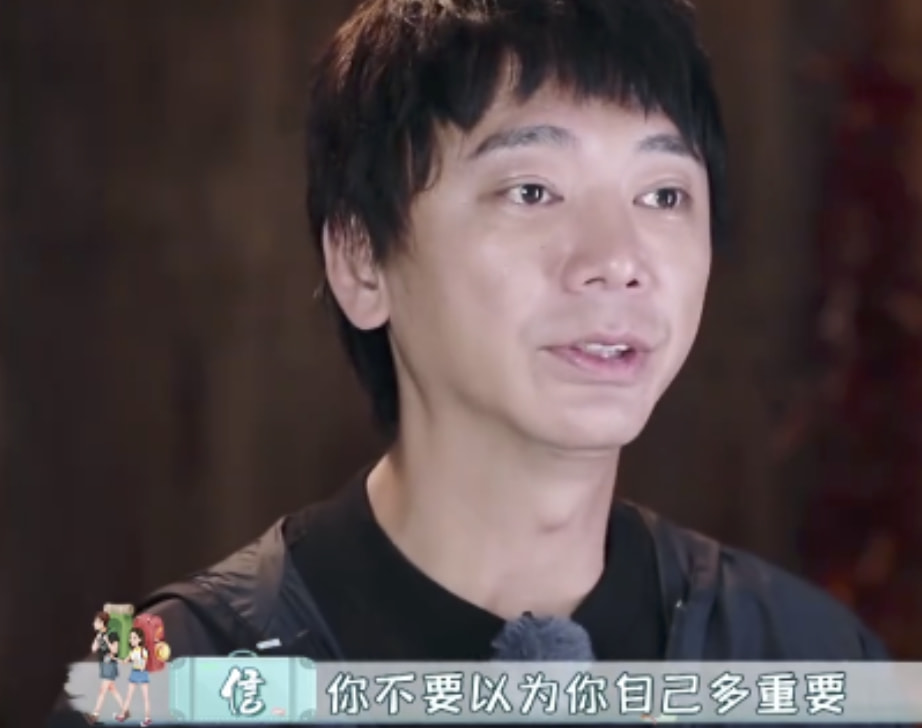
從此,放下負擔,重拾清閑。
這樣的與世隔絕,催生出一個真空層,沒有任何縫隙可供外界侵襲。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過濾雜質,遵時養晦。
投以自律,專注創作。
反躬自省,正己修心。
活得自我,亦活得純粹。
重要的是,認清了自己。
這份自控延續到了舞臺。

每場演出前,信都會戒酒,儲存體力,保持狀態。
胸聲拉扯式演唱,超負荷,費嗓子。
容不得半點差池。
2013年,信在內地商演。
唱到成名曲《死了都要愛》。
臺上歌聲,穿云裂石。
臺下歌迷,撕心裂肺。
唱到高潮,粉絲奮不顧身,沖上臺獻花給信。
信看到花,眉頭微微一蹙,他接過花,而后放下。
大發雷霆:“唱歌的時候不要送花。”
臺下噓聲不斷。

主持人董卿見狀,當場打抱不平:“唱歌很重要,做人更重要。”
滿場歡呼。
對信的指責聲,一浪高過一浪。
逐漸發酵成他丟花砸人,對粉絲耍大牌。
引起街談巷議,輿論甚囂塵上。
眼看聲浪不斷,一度無法挽回。
經紀人出面打圓場。表示,信只是把花放在地上。
信本人也親自發微博致歉:
“對于那位給我花的人,很抱歉,傷了你的心也傷了大家的心,我對于表演有一定的堅持,但沖動的個性讓我的行為做了不當示范,謝謝董卿小姐指正。”

但對表演,信仍堅持己見。
在文末呼吁歌迷,應在不打擾的前提下送花。

信從不否認自己的沖動。
于他而言,音樂與舞臺,是原則性問題。
底線不可越,規則不可違。
他謹記于心,且篤之于行。
對舞臺如此珍視。
源自于信坎坷的出道史。
信,不是幸運兒。
音樂世家,家境優渥,天賦鋪路。
通通與他無關。
入行之前,他端過盤子,在酒吧駐唱。
袋里只有幾個銅板叮當響。

常年看老板與客人的臉色行事。
信深知何為苦。
臺下的觀眾,要么有錢,要么有槍。
他只能言聽計從。
練就了一身喝酒本領,一次猛干5瓶白的。
有時臺下鬧事,槍聲響起,他仍能面不改色,繼續演唱。
駐唱十余年。
途中,被星探發掘,簽約掛名滾石。
可滾石,是五月天阿信的主場。
一山怎可容二“信”?
滾石待了三年,信仍一事無成。
他感到非常挫敗,躲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
手里夾著一根廉價煙,腳下全是空酒瓶。
茫然若失。
而立之年將至,仍郁郁不得志。
一瓢瓢苦悶澆灌著他。睡不著覺,他徹夜創作,寫歌,練唱。
常常唱到聲帶充血,發不出聲音。
提不起勁,他狂聽唱片,模仿,學習。
“與其茍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
信對自己說。
2002年。
命運迎來轉機。
信被日本唱片公司“艾回”簽下,組成搖滾樂團——信樂團。

以《死了都要愛》《天高地厚》《離歌》……將“信樂團”這把搖滾之火,燒遍兩岸三地。
作為主唱,信的狂妄吶喊,憤怒叫囂,唱出一代人嘶吼的青春。
30歲,終成名。
從地下走到地上,他花了13年。
這一路,心懷感恩。
但。
公司提供的,是機會,亦是束縛。
成名后,頻繁被要求著奇裝異服演出,日復一日地唱《死了都要愛》。
風格,單一。
形式,枯燥。
蟄伏多年,無任何進步可言。
信疲倦不已。
所以,合約期一到,他立馬宣布單飛。
面對“白眼狼”爭議,信很平和,只說了句緣分使然。
2007年,信單槍匹馬,勇闖娛樂圈。
一年一專。
多棲發展。
拼命至極。
娛樂圈,新人層出不窮。
信的發展,后繼乏力。
而后,聲帶嘶啞,幾近失聲,聽力受損,皆為常態。
信卻很慶幸,幸好嗓子還能恢復,還有另一只耳朵可以用。
一路苦難,他細嚼慢咽。
這樣的人,怎能甘愿被馴服?

再后來,他去音樂綜藝。
信很珍惜,也很困惑。
珍惜舞臺來之不易。
困惑樂壇止步不前。
2002年,他以翻唱作品初試啼聲,攪動樂壇。
2022年,仍是翻唱作品橫行霸道,盤踞樂壇。
自己是樂團出身,唱翻唱成名。
雖受追捧,卻常有抬不起頭的感覺。
20年過去,樂壇依然如此,怎能不叫他失望?

頂著被同類節目封殺的風險。
信豁了出去。
赤手空拳,撕下樂壇最后一條遮羞布。
有人稱他,頭腦清醒,嘴直心快。
有人罵他,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
一番話,得罪了半個樂壇。
但又如何?信不在乎。
他在乎的。
是停滯不前的音樂。
是搖搖欲墜的樂壇。
是前路渺茫的自己。
若原創作品無法進步,樂壇早晚面臨枯竭。
信甘愿跳出來,當這個惡人。
得罪了一圈人,卻也拽住了樂壇的生死線。
贊他耿直也好,怪他魯莽也罷。
信全都認。
樂團難有出路,原創頓足不前。
他以清醒,以態度,拽動樂壇,讓其墮落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唯有如此,才能捍衛音樂與音樂人的尊嚴。
若要細究。
他無非是——
所認定的,路雖遠行必至。
所鄙夷的,不屑與之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