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王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
要論清末革命黨中對于中國未來政治建設問題思考最深入者,則非章太炎莫屬。他十分熟悉中國歷代典章制度,并閱讀了不少近代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的論著。
1906年,因“《蘇報》案”而入獄的章太炎,終于得以出獄,并再次東渡日本。此后他的思想,較之先前,一大變化就是開始深入反思西學對中國歷史與現狀的適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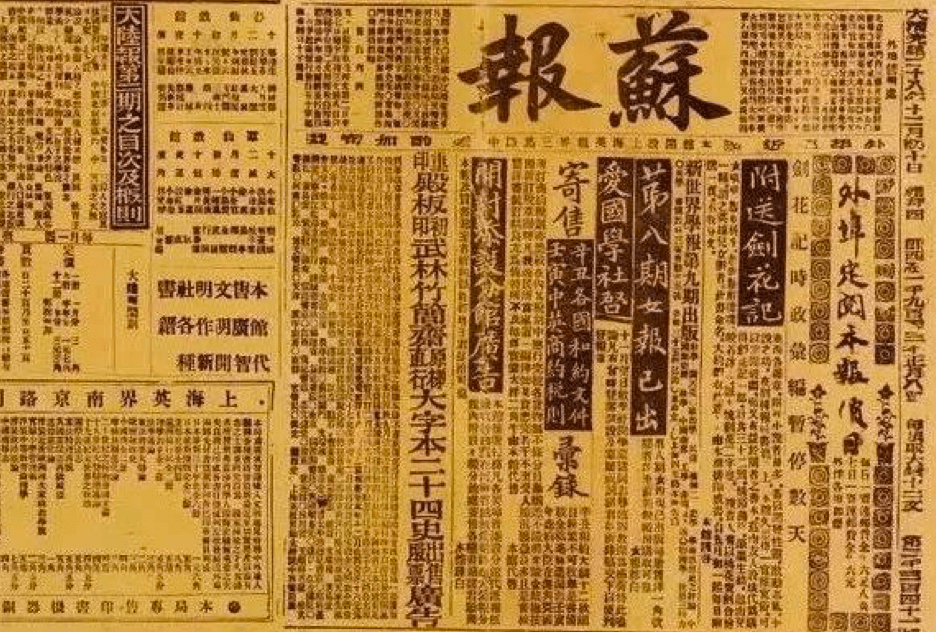
近代 1902年《蘇報》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國內第一份報紙,1896年6月26日創刊于上海。章太炎、柳亞子等在《蘇報》上發表過文章。1900年后由宣傳改良轉為傾向于革新。1903年,“蘇報案”震動全國,促使革命運動迅速興起。
他認為“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
(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中國的發展,不應處處模仿他邦,而是應以本國歷史與現狀為根據,思考真正適合于中國自身的立國之道。
(章太炎開始反思西學,一個不容忽視的緣由便是他由于“《蘇報》案”而入西人監獄,在獄中飽嘗苦頭,使他開始質疑西人宣傳的“文明”、“民主”是否真的名實相符。參見章念馳:《滬上春秋——章太炎在上海》,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版,第32—33頁。)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對于中國古代典章制度,不能輕易用“專制”二字簡單概括,而是應探尋其中的歷史沿革與內在原理:
我們中國政治,總是君權專制,本沒有什么可貴,但是官制為甚么要這樣建置?州郡為甚么要這樣分劃?軍隊為甚么要這樣編制?賦稅為甚么要這樣征調?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將專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殺。就是將來建設政府,那項須要改良?那項須要復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見諸施行。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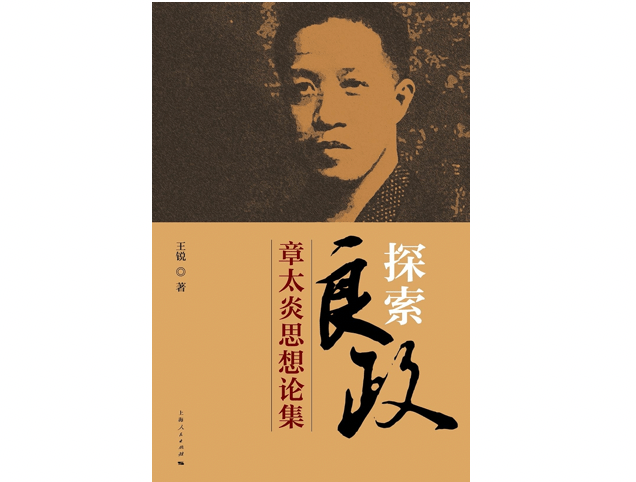
《探索“良政”:章太炎思想論集》,王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嚴復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
作為被近代西方所宣揚的帶有規律性的“條例”,主要伴隨著19世紀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生,特別是被用于向非西方地區宣揚西方文明的進步性與普世性,究其實,并無放之四海皆準之理。認識中國問題、解決時代危機,須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歷史進程,從中歸納總結蘊含原理性質的、具備解釋力的“條例”。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當時無論是革命派或立憲派,包括清廷內部的改革派官員,都認為未來中國的制度設計應借鑒近代西方的代議制,只是存在著認同共和政體或君主立憲政體之別。而章太炎則一反潮流,主張代議制不可照搬于中國。在《代議然否論》一文里,他認為代議制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制息息相關,議員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封建貴族的政治地位。而中國自魏晉以后,社會上除了君權,已基本沒有世襲性的政治權力,因此不適合移植代議制度,人為的制造一個特殊的權力群體,他的這番思考,根植于他對歷史的重視,即歷史流變是思考制度問題的重要參考,是否與歷史接榫也是一項制度是否具備基本合法性的重要條件。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此外,他強調制度建設應和中國最基本的現實國情相符,在中國廣土眾民、地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條件下,能夠被選為議員的,很可能是地方上的豪右富民,他們不會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這一觀察,注意到了近代政治體系里權力、階級、資本之間復雜的關系,制度移植需要針對基本國情具體分析,世間并無一種普世主義的制度。這在視西方憲政體制為天經地義的清末民初,尤顯空谷足音。

章太炎研究范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最后,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里設計了一套他理想中的制度。
簡要言之,他主張總統只負責行政與國防,外交上作為國家禮儀的象征,此外不再具有其他權力。另外,司法獨立,其主要負責人地位與總統匹敵,但凡政治上與社會上的案件,皆由司法部門負責,不受其他權力機構干涉,即使總統觸犯法律,也可依法將其逮捕。立法不由總統干涉,同時杜絕豪民富戶參與,由“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18頁。)除了小學與軍事學校,其他教育機構皆獨立,其負責人與總統地位相當,以防行政權力干預教育,因為“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殠敗,而矯健者常在民間。”在任免問題上,章太炎堅持總統任命,“以停年格遷舉之”,(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18頁。)
按照其任官時間與功績來按部就班的升遷。其他政府官員的正常任命不容總統置喙,除非前者有犯法與過失的行為。若總統或其他官員有瀆職或受賄等罪行,人人得以上訴于“法吏”,由后者傳喚嫌疑人,審理其案情,在量刑標準上,輕謀反罪,以免民眾被肉食者威脅,但叛國罪則重判,特別是割地賣國行為一律處以死刑,以示國家主權不容破壞。在政策執行上,凡必須由總統簽署之政令,一定要與國務官聯署,保證有過失總統與其他官員共同承擔,杜絕諉過于下。每年將政府收支情況公布于民,以止奸欺。因特殊原因需要加稅時,讓地方官員詢于民眾,可則行,否則止,若正反意見相差不大,則根據具體情況處理之。在正常情形下,民眾不須推舉議員,只有面臨外交宣戰等緊急時刻,則每縣可推舉一人來與聞決策。此外,他還設計了相關經濟政策,如只能制造金屬貨幣,不能制造紙幣;輕盜賊之罪,以免法律淪為富人的幫兇;限制遺產繼承的數目,防止經濟不平等世襲化;杜絕土地兼并;工廠國有化;官員及其子弟不能經商;商人及其子弟不得為官。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總之,章太炎認為一項好的制度,應該真正體現人民民主,而非成為新的壓迫工具,應代表最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而非代表各類新舊權貴豪紳的利益,并能克服近代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諸弊端,讓民權思想得以名副其實的在中國生根。此外,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時代主題,任何制度設計必須顧及于此,即維系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動員廣大社會力量參與國家建設,而不應人為的制造地域隔閡,撕裂民眾的國家認同。
章太炎批評當時講政治的新派人士“法理學、政治學的空言,多少記一點兒,倒是中國歷代的政治,約略有幾項大變遷,反不能說。”
(章太炎:《常識與教育》,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第63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本乎此,在1908—1910年間,章太炎發表了多篇論述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章,如《官制索隱》、《五朝法律索隱》、《秦政記》、《說刑名》等,努力挖掘其中蘊含的平等精神、重視弱者生命、抑制權貴等因素。
比如在《秦政記》一文里,章太炎試圖挖掘深刻影響中國兩千余年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的秦政之精髓,從中總結中國古代政治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內在原理,以此作為未來中國制度建設的歷史參考。章氏自言中國的政治應“依于歷史,無驟變之理”,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載虞云國整理:《菿漢三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頁。)
因此《秦政記》不但是他嘗試對歷史提出解釋,更有著極強的現實指向。他強調理解秦政不可簡單套用源自近代西方的“專制”話語。秦政的運作,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平民的利益。并且在銓選人才方面,秦制具有古典式的社會流動性,實踐韓非主張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有效動員了當時的基層社會力量,杜絕皇族貴戚弄權干位,樹立了良好的政治風氣。此外,秦政厲行法治,賞罰一準于法,拒絕對特權集團法外開恩,這一點體現了社會平等,同時形成流傳后世的政治文化傳統,此乃未來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傳統資源。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又比如在《五朝法律索隱》一文里,章太炎認為立法之事應本于中國現實狀況,對于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社會道德、風俗、習慣應予以充分重視,使得法律條文能和廣大民眾的生活習慣相吻合,在維護社會基本秩序、改革已經不適合時代風氣的社會弊端同時,不去人為破壞民間習之已久的基本生活方式。他通過疏解五朝法律相關內容,強調制定法律應從平民的立場出發,以保障平民權益為旨歸。就此而言,五朝法律中所體現的“平吏民”、“恤無告”諸特色,尤值得后人充分參考借鑒。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此外,伴隨著中國被卷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章太炎對中國國內中西資本力量的擴張十分警惕,擔心在創辦新政、發展工商業的名目下,廣大平民遭受新式壓榨與剝削。因此他表彰五朝之法頗有“抑富人”的特征,其根本精神足以為當下如何通過法律形式抑制資本的力量提供思想資源。章太炎之于五朝法律,考史其名,鑒今其實,表達了他對政治平等、社會公平,以及每一個生活于中國大地上的人都能真正獨立、免于壓迫的強烈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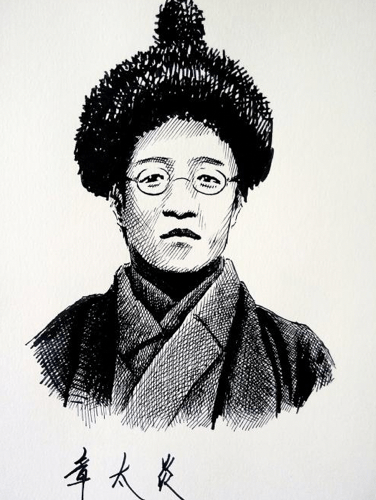
章太炎。
武昌起義爆發之后,章太炎回國參與新政權的建設,他目睹當時盛行的參照西洋各國政治建制來探討未來中國的制度建設,強調為政者應做到“先綜核后統一”,即對中國廣土眾民且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有充分的認知,在明晰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對癥下藥,通過有效的政治治理,來“鞏固國權”,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避免列強染指。因此他對講求西學的政壇新銳極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憲派與清廷的舊官吏,依靠他們的行政經驗來穩固政治與社會局面。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另一方面,基于實現民權的理想,他對新成立的臨時參議院與其制定的《臨時約法》展開批評,認為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眾意志。《臨時約法》中賦予參議院極大的權限,章氏則強調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參議院中的參議員并非根據民意而當選,既如此,后者的政治行為無異于越俎代庖,因此在法理上并不具備合法性
特別是第二點,基于他在清末發表的政治主張,在《臨時約法》頒布之后,章太炎并不像國民黨人那樣,認為此法之目的在于體現民權,而是質疑其中的關鍵條款,否認其正當性。他指出: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國民為共和國主人,有主權者。參議員為都督府差官,無主權者。故國民對于參議院之《臨時約法》,有不承認之權,此最簡明之理由也。
(章太炎:《否認<臨時約法>》,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冊第419頁。)
可以看到,章氏認為《臨時約法》為臨時參議院所指定,而后者的成員究其實只是各省獨立之后所派遣的代表,只能體現各省首腦的意志,并不能真正代表作為“共和國主人”的全國國民。如果按照主權在民的理論,那么國民就有不承認此約法的權利。根據同樣的理由,章太炎認為《臨時約法》第二條所規定的“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實難成立。因為“今日足以代表國民者,為參議員乎?而參議員為都督所派,絕非民選。為遵照此次《約法》之選出者乎?而第十八條之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假令又有都督選派,甚或有自署為參議員者,亦《約法》所許。以此組織參議院,果足代表人民全體而行使主權乎?稍有政治常識者,必不謂然。”
(章太炎:《否認<臨時約法>》,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冊第419—420頁。)文章來源
http://news.sohu.com/a/411213433_120132027
http://news.sohu.com/a/411248212_120472015
http://news.sohu.com/a/411248212_120472015
http://news.sohu.com/a/411275466_120132027
http://news.sohu.com/a/411274470_120132027
可見,章太炎所在意的,是參議員是否真正能代表民眾,此實則亦顯示出他對武昌起義之后由士紳及其代言人所主導的政治局面頗不認同。
《臨時約法》第四條曰:“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對此章太炎反駁道:
夫第二條既言主權在國民全體,而此條行使統治權,乃由非國民所選之參議院,殊不可解。主權絕對不可分離者也,屬于國民全體,其行使不必國民全體可也,斷不可不由國民所委任之機關。今之參議員,非由國民委任,何能有此特權?此第二條與第四條互相抵觸也。
(章太炎:《否認<臨時約法>》,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冊第420頁。)
此處章氏聲稱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且不可分離,很容易讓人想到盧梭的理論。盧梭認為主權是公共意志的體現,如果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那么就只是一種行政行為或一道命令,不能體現主權。同樣的,主權也不能被代表,因為意志不能被代表,只能是此意志或彼意志,絕不存在中間物。
((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3、120頁。)
章太炎曾稱贊盧梭“能光大冥而極自由”,復于清季的政論中時常借用盧梭的學說。
(朱維錚:《<民報>時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5期,第43頁。)
此處為了論證參議員不具合法性,很自然的他會再次援引盧梭之論。不過他同時主張主權的行使不必經由國民全體,只需國民委任的機關由國民選舉出來即可,這與盧梭所強調的主權不可被代表又不盡相同。或許仍然考慮到國權問題,即如何保證政治秩序的穩定,所以章氏對盧梭的直接民權說有所保留。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民主政論家和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開創者,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新愛洛伊絲》《植物學通信》等。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法學家阿克曼認為,在共和政體下,一旦憲法未能處理好總統與國會的關系,那么二者之間互相對立的權力會運用憲法所賦予它們各自的權利來互找麻煩,國會不斷攻擊行政機關,總體不放過任何可以擺脫國會束縛的機會,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治理能力的危機”。
((美)阿克曼著,聶鑫譯:《別了,孟德斯鳩:新分權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
章太炎所觀察到的民初政局在某種程度上正好印證了這一觀點。在制定《臨時約法》時,國民黨人希望借擴大參議院的權力來限制袁世凱,對此章太炎洞若觀火。出于“鞏固國權”的立場,他指出《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任命國務員及駐外人員須經參議院同意這一條款極不合理,易于導致“以立法院而干涉行政部之權,該院萬能,不啻變君主一人之專制,而為少數參議員之專制,且同意之標準難定,稍有才智之士,鮮不為人猜忌,自非鄉愿不能通過。”同樣的,該法規定國務員一旦受參議員彈劾,大總統應免其職,此舉將使參議員“濫用此非常之大權”,勢必造成“國務員更換之頻繁,雖灶下爛羊,亦將膺選,何暇謀政治之進行乎?”
(章太炎:《否認<臨時約法>》,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冊第421—422頁。)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議會政治后,他對黎元洪痛陳:“中國之有政黨,害有百端,利無毛末”,在參議院中忙于政治博弈之輩“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長此不息,游民愈多,國是愈壞。”
(章太炎:《與黎元洪(1912年)》,載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384頁。)
由此可見,章太炎認為名實不符的議會政治不但無補于伸張民權,而且還會影響政治穩定,對國權造成極大損傷。
但章太炎的基本困境在于,他曾希望借助舊官吏與立憲派的政治經驗來根據中國現狀施政,但對后者的真實面目有所認識之后,便寄希望于作為國家元首的袁世凱能厲行法治,制裁貪瀆敗政之徒。一旦發覺袁世凱實為此輩的最大庇護者,章太炎又開始與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謀大計。可國民黨當時無權無兵,非但不能改變現狀,反而因“二次革命”失敗致使實力大損。在章氏的政治視野里,作為主權所有者的廣大國民始終是“沉默的大多數”。
章氏所仰賴的政治實踐主體,只是從立憲派與舊官吏到國民黨人之間轉換而已。無法找到新的政治主體;無法借由組織動員新的政治主體自下而上地徹底推翻舊的政治毒瘤,重建政治組織,達到政治整合;更無法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不斷地實踐來真正認識中國社會的復雜性,總結出一套既能符合中國現狀,又能讓大多數新的政治主體獲得參與感與翻身感的政治理論,這或許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爭中處處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作為政治實踐者的章太炎留給后人的最大教訓。在這里,雖然他依然認為中國古代制度乃是“專制”政體,但也開始注意到必須仔細梳理沿革、總結得失,“改良”同時猶有可“復古”之處存焉,這樣方能為未來的制度建設奠定基礎。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經將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思考建立在從中國歷史自身脈絡出發,明晰當下具體的實際形勢,考量本國各類制度利弊,視此為制度建設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評當時作為引進西方政經學說之代表人物的嚴復“所譯泰西群籍,于中國事狀有毫毛之合者,則矜喜而標識其下;乃若彼方孤證,于中土或有抵牾,則不敢容喙焉”,即將西方的歷史進程視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中國歷史與現狀,導致遮蔽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現實的獨特性。章太炎指出,這一認知模式,“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歷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復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當然,據今人研究,嚴復的翻譯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論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于時人對“民族”等近代術語的理解與界定頗不一致,這一知識儲備的差異性,也導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沖突。參見王憲明著:《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