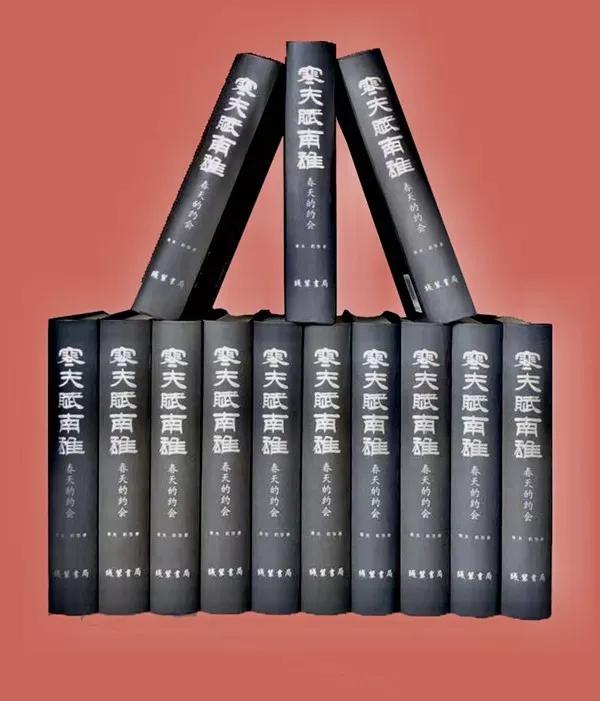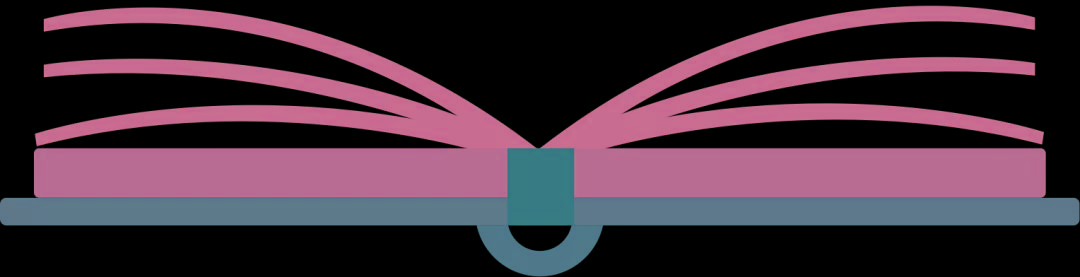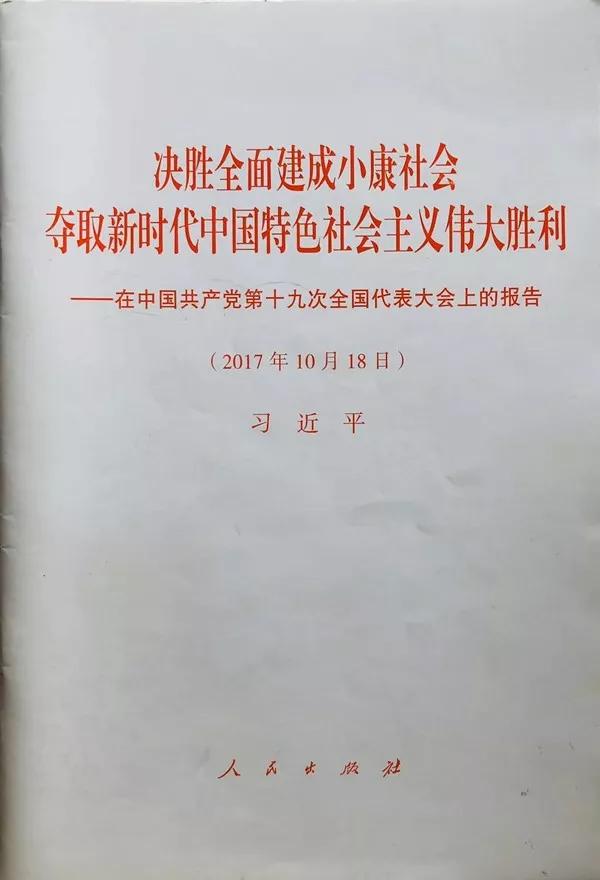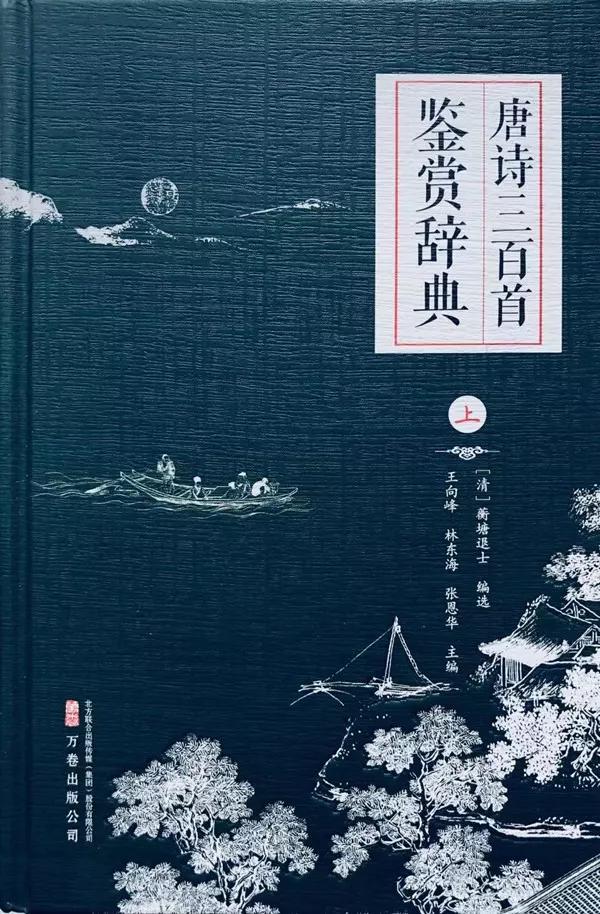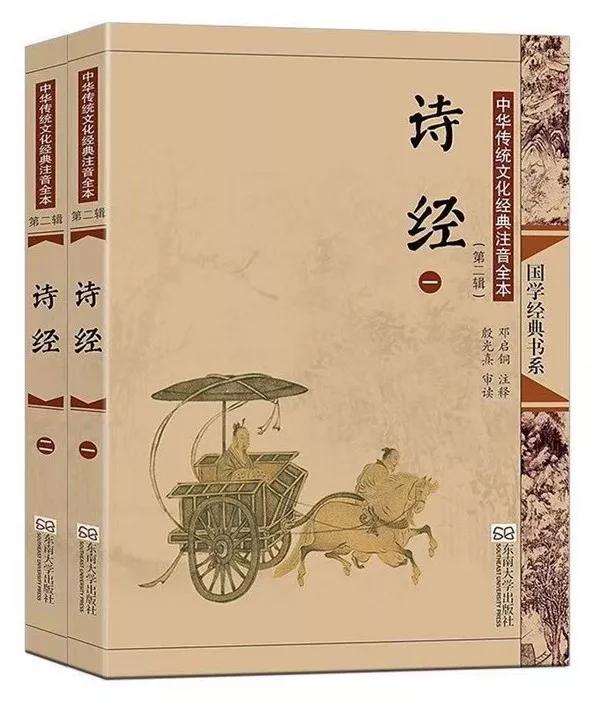當代學壇騏驥寒夫
《論“詩”當為民而“歌”》論文專題
作者|寒夫 主編|幽夢靜美
寒夫名言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為群眾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首先,《講話》和毛主席本身就具有了千古不朽、萬世流芳之歷史意義。因為他將“群眾問題”與文藝工作者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倘若,我們當下的文藝工作者將廣大人民群眾亟待關心之住房昂貴、老有所憂、醫療保險及“死不起”等問題,以藝術之形式反映出來,這對未來人類而言,豈不是《講話》精神之延續和實踐嗎?……否則,我們廣大的文藝工作者都在干什么去了呢?
—— 寒 夫
【寒夫藝術簡介】
寒 夫:姓孫,學名孫勇,乳名慶國,字樂天、子夫、赤壁山人等。1965年湖北黃州浠水蘭溪出生。兩歲由家父引領習書,后學古詩詞及國畫。十余歲便通讀《詩經》《離騷》等;十六歲完成第一篇哲學論文《關于〈共產黨宣言〉》。
2000年6月18日于深圳博物館隆重舉辦“寒夫書畫藝術作品展”開幕式。
2003年金秋由中國人民友好協會、團中央等八家單位于北京臺基場友協珍藏館共同主辦“寒夫藝術成果報告展”。
2007年《滁州三秀》榮獲“紀念歐陽修千年誕辰”全國征文金獎。
2008年書、畫作品榮獲“迎奧運”金獎。
2010年美學巨著《寒夫藝術論叢》于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暨學術成果研討會。
2013年哲學巨著《藝術家眼中的馬克思主義》(史詩部分與理論部分)由中央編譯局舉辦首發座談會暨寒夫思想、學術成果研討會。
2015年文學巨著《寒夫賦黃州》(多體文集)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審定為當代文學經典。
2018年5月5日由全國政協《人民政協報》舉辦“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 寒夫書畫文主題藝術展”于北京炎黃藝術館隆重開幕,其反響空前轟動。
2019年暮春《寒夫長篇古典詩詞·組詩》入選《中國當代詩歌大辭典》并榮獲一等獎。后該書出版成為央視臺“至尊禮品書”。2019年金秋與南雄市委共同推出多體裁文集《寒夫賦南雄•春天的約會》隆重首發。此作乃作者第二部由國家級出版社審定為“當代文學經典”。
此外,寒夫詩、詞、賦名篇等,被全國多處人文景區勒碑及摩崖石刻。其書畫作品由國際多國政要及文化機構廣為收藏。書法方面,他開創了中國文字以來“行意甲骨文”之獨特體貌;其繪畫注重人文畫的山水、花鳥與人物多重美學內涵的完美融合;其文學以“兼濟天下”為使命。并于詩、詞、歌、賦、論、評、哲、書、畫等領域卓有成就,且于世獨立。
論 “詩” 當 為 民 而 “歌”
—— 中國文學史上即將消失的文明
【按語】
中央強調:“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提升文藝原創力,推動文藝創新。倡導講品味、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基于此,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學家、詩人、辭賦家、藝術評論家、文藝批評家、書畫藝術家寒夫,便是踐行這一“文藝導向”而孜孜以求地進行其多領域藝術創作實踐及社會實踐。不啻如此,寒夫尚以半個世紀之親力親為踐行孟子:“人有不為者,而后可以有為。”之君子風度虔誠的傳播大道學說和藝術耕耘。
他深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源泉,其重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文學藝術作品,這也最能表現個人的思想文化水準”。于是,長期以來,寒夫的思想傳播、學術研究、藝術創造等無不吻合其所處的時代節拍、民族復興、家國繁盛。他認為,作為思想家、學者、藝術家們,不為人民吶喊,不為國家思考,只一味自私地視名利高于一切,于是飽食終日、尸位素餐、渾渾噩噩、浪跡虛名,夫此行同狗豨、茍且偷生的植物之群,既對不起人民的養育之恩,也對不起家國所賜予的盛世環境;想必、又怎能對得起人之初期許“望子成龍”而造福天下之父母夙愿乎?!所謂文化,就是用文化之陽光雨露去滋潤大地;所謂知識,就是以知識去凈化人們尚未開啟渾濁之頭顱!身為文藝工作者,便更無條件地應履行于這一意識形態之最前列。是謂憂國憂民之范式,是謂人類遠征之騏驥耳!
【原文】
早在《詩經》(孔子著)里,至圣文宣王就設定以“美刺”來衡量天下詩人、作家及相關著書立說者是否堅守這一創作之道德操守。“美刺”之“美”,乃贊美、謳歌、歌頌;“刺”:乃諷刺、諷喻、抨擊也。同時,孔子還強調“文筆有用”之學說主張;即以優秀的文學作品去反映天下人(泛指勞苦大眾)亟需關切的社會問題。否則,那些作品何以謂為“有用”之作呢?后繼孟子之一代大儒韓愈揭竿而起倡導說:“文以載道!”這是說,一切從文者,務必以作品去向天下人傳播人類師法自然之規律;否則,世人何以知“道”(泛指自然規律)哉?
一言以蔽之,這些偉大的圣哲警醒天下從事作文章及授業者,旨于以觀察家之責任感與使命感去理性地用文學作品謳歌天下的“真、善、美”和批判“假、丑、惡”劣跡的同時,還務必不失時機地告誡人們遵循大道學說,并警醒世人只有“大道學說”,才是引領人們走出昏聵的精神泥潭,最后邁向覺醒、開明的“無為”捷徑。上述乃讓我們為文者明白何以“美刺”同“文以載道”之職業規范和道德良知,以期更好地排檠天民及家國大道至簡且漸行漸遠!
然則,我們的文學先賢,他們是如何為廣大勞動人民吶喊他們同厄運抗爭的呢?唐·李紳在《憫農》里寫道: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此作的“點晴之筆”便是“誰知盤中餐?”詩人為何這樣寫呢?倘若用別的語句替代,自然,就失去了詩人“替天行道”的擔當意識。那么,詩人的“誰”究竟是在問誰呢?毋庸置疑,詩人之問,自然是針對封建統治階級,只有他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才不知天下勞苦大眾的“汗滴禾下”之苦難!此詩雖20字,然,卻如同無聲之炸彈投向那個黑暗腐朽昏聵的政治集團。再細品下一首,李紳這樣寫道: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
四海無閑田,農父猶餓死!
稍有仁心者,無論哪種階級的文人,讀到這里,無不潸然而淚、痛心疾首!那些在苦難中掙扎的農民,他們在春天寄希望于田產,一顆顆地種下期盼的種子,經歷長年的耕耘,秋后才拾得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莊稼人,他們怎奈何得了那大權在握且一手遮天的統治階級呢?如果作為一位有階級情感和人文化育的靈魄,又怎能想象不到“四海無閑田,農父猶餓死”的血淚控訴是在何等程序上直指封建王朝統治集團的與民為敵的要害之處呢?尚且,李紳此等高尚的節操和大無畏的人文膽略是一般蠅營狗茍、尸位素餐、無病呻吟的沒落文人所能比肩的嗎?唐·白居易與李紳同年出生且又同年作古,但“白詩”就顯得更有氣勢,更有內在的暴發力!在《賣炭翁》里白居易這樣刻畫道: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如此清晰白描的忍饑受累的求生場景,設若我們的封建官僚稍作一下憐憫,那年邁的“衣正單”的老翁何以大雪封路之時去忍受饑寒交迫之痛呢?難道當朝的統治者是沒長眼睛,還是從未見過此等凄愴景象乎?恰恰相反,那些代復一代的宮廷狗官們,他們不是不知良人在遭遇人為和自然界的雙重嚙噬,他們是在享樂與宮廷粉黛佳麗們的醉生夢死之中,怎能將此下里巴人之苦難放在心里呢?白翁借助“炭翁”之苦,深刻折射出反動統治階級草菅人命、權力至上卻又毫不作為的罪惡本性。但在《長恨歌》里,他那批判的力量猶為令人敬佩;他這樣揭示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這里,詩人開門見山地揭示出了歷代昏君腐朽和草菅人命之共性。白翁這里開篇以“漢皇”劉徹托出當朝的唐玄宗,其技法乃為把握文學藝術表現內在之需,決非為寫“漢皇”而寫劉徹;正因為通過對劉徹作為“引子”才順理成章地托出本朝同類之“權貴”(玄宗帝)昏庸之重演。雖則,兩句一韻14字,然而,為晚唐之命運深深地埋下了伏筆。所以我們千百年來的讀者沒有不敬畏《長恨歌》乃揭露歷上最昏聵君王的力作之一。因為庸君大都驕奢淫逸,故,白翁寫道: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人們不難想象,這樣的君王,在亂世里肆無忌憚地縱情作樂,他又怎能看得見天下“賣炭翁”之類的悲鳴與凄愴呢?這里,自然為王朝的傾覆作了無形的鋪墊。
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玄宗帝不僅將寵愛聚于楊貴妃一身,同時,還要使盡天下美女三千之多作為貴妃之陪侍,可想這位貴妃受寵之樂到了何等的極至,同樣又反襯那昏聵無度的所謂君王到了何等程度的脆弱啊!不僅如此,尚且,那三千多佳麗,絕大多數終生未得到過君王的福報;可想,那天下的農父、炭翁等底層階級又如何分享到皇權的福祉呢?回答是自然的!那三千多佳麗的三千多父母又有幾位不因未成人之女便奴入皇宮而讓其父母在憤懣中渴望女兒早日回家團聚的呢?委實的殙王,從來是不思家國或改朝換代之命運!這在罪惡里的李隆基同樣無法料到厄運的降臨,但這厄運的到來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接著,順著唐玄宗目無人民、悖逆天道之惡報的升級,其大亂早已擺在了眼前,只是因為昏聵與麻木而無法覺察罷了。白翁詩中這樣寫道: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軍萬馬西南行。
荀子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就是說,天下的人民既然可以承認他作為一國之君;當他昏庸無度、荒蕪朝政,導致家國大廈坍塌時,人民自然要以摧枯拉朽之勢打倒他、埋葬他!昏王在人民覺醒后被追剿逃往西域的路上,竟然此般狼狽不堪。白翁接著寫道: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域都門百余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苦難深重的人民,將骨子里積貧積弱之怨一起匯成了復仇的火種!是樣,在人民的反抗聲中倒下神壇的萬惡反動的統治者,他與歷代昏君的下場同出一轍;自古以來又有誰能抵抗住了由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洪流呢?論及唐玄宗李隆基,這里,筆者不得不推延一下:古往今來,甚而古今中外,哪一個新政權之建立,不是因為舊朝之腐朽與墮落而為自己掘就墳墓的呢???
現在,人們看到的是,昔日那寵愛一身的楊妃的蒙昧無知、溝瞀任性、不憐天民、驕奢淫逸、飽嘗皇恩,日漸趨為妲己及喜妹而致使李隆基不理國政、不恤民苦、土崩瓦解、走投無路。如今,政權易幟,昏君心愛的美人兒被勒死在歷史的馬嵬坡上,難道這一切不是昏庸之君因喪失理性、草菅人命所招致的莫大的報應和天大的諷刺么?相反,假如,唐玄宗深諳與民同樂之理,撫民問苦之道,豈有這般西逃政變、安祿山發難、百姓怨恨載道以至于將“貞觀之治”斷送在這一個荒蕪國政,昏昧之君的手里呢?因此,綜合歷朝和本朝之亡國史,筆者認為:歷朝歷代的暴政和君王最不值得歌頌。其一,它喪失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天下意識;其二,它御用佞臣和碩鼠而導致亡朝亡國;其三,它揮霍和耗廢民脂民膏還肆意與民為敵;其四,它享用人民賦予無限的俸祿即使做得多好的政績亦乃本分之事,更何況少有百姓滿意之政績者;其五,它一手遮天,好大喜功,請功邀賞,且悖逆法度而招致天下烽煙四起、生靈涂炭。如此泯滅天道、戕害人倫的植物之群,還有何顏面強迫人民為它歌功頌德的呢?要歌功頌德的只有兩種人:一是人民,因為人民創造了歷史;一是圣哲,因為圣哲總是在引領人類前行的科學航向!
下面我們再看看唐代另一位早于白翁半個世紀的千古詩圣——杜甫是怎樣為民請愿的。天寶七(748)年創作的后來成為不朽詩篇的《兵車行》一開局就為讀者展開了一幅因戰爭給天下人民帶來的征戰之苦與妻離子散的雙重迫害;杜甫寫道: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
古往今來,人們見過戰亂的頻起,但,若為自由而戰、為保家衛國而戰,作為軍人走向戰場,自然天下的父母一定帶著仇恨,充滿信心地吩咐兒子要有血腥膽魄,在戰場上沖鋒陷陣、驍勇殺敵,或為了解放,抑或為了誅殺叛賊等建功立業報效家國。然而,748年前后的唐代宗李豫拒絕忠良、御用惡小而最終戰亂頻發,國無寧日。于是這時的征兵,人們不是為了保家衛國或開國剿匪,而是因為昏君誤國、暴政怠業繼而招致兵燹戰亂、窮兵黷武。自然,此時此刻逼上戰場的兵士等,又有多少是樂意為這樣的昏聵無能之君去賣命送死的呢?!……
本來積貧積弱的父母,又遇上這般兵荒馬亂的拉夫抽丁,身為人父人母誰還能盼到兒子會從戰場保命歸來啊!因此,這樣地在集體拉丁抽夫倉促上戰場,天下還有誰的心不在顫抖呢?尚且人們看到過去從十五歲打仗到現在頭發花白尚在邊界參戰;這又怎不令為即將參戰的兵士的父母痛心疾首啊! 杜甫沉痛地寫道: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戌邊。
是經年的狼煙四起,所以人們相送兒子參戰便是這樣一幅悲慘畫面。 杜公還寫道:
由此可見,代宗李豫時期的戰亂不僅僅一兩次使全國士卒飽受愴傷,而是經年的狼煙四起,所以人們相送兒子參戰便是這樣一幅悲慘畫面。 杜公還寫道: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可以想象,那個戰火紛飛,人心慌慌的歲月,別說失去壯漢無法保收,即使男丁多的家境也難以保持豐收年景。杜公如此細致的觀察與刻畫,正反映了他時刻將目光投向飽受悲鳴的黎民和那悖逆天道、無視天良的反動的統治階級;正因為他們的昏庸無能、荒蕪國政、目無天民、違背天道才導致普天下人民無法脫離水深火熱的存系之故。在《兵車行》接近尾聲時,杜公這樣控訴道: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人們本來在飽嘗朝廷抽丁拉夫之痛,可那萬惡的帝制還肆無忌憚地加重農耕稅賦,這讓饑寒交迫的人民更是走投無路、雪上加霜!于是,可憐的勞苦大眾,他們在莫名的苦難中開始總結出了一個新的規律——杜公這樣“叛逆”地寫道: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在這般巨痛里,因為誤國的戰亂就連人類的本以規制的生存秩序都漸漸被扭曲:人們嘆息說生了女兒還可以嫁入鄰居以免于戰場上的血光之災;生了男兒相反成人后還要送往萬劫不復的戰場上為那腐朽無能的昏君活活送死!這樣悲愴的時世,還要生兒(男性)干什么呢?詩的結尾處杜公這樣哀哀地訴說道: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可憐啊!這些為昏君而征戰的血腥男兒,他們——在戰場歷經幾多非人之痛,自然不會有人得知,最后就連他們有去無回的白骨都不會有人為他們收斂一下!這是多么可怕的現實、多么恐懼的王朝、多么令人泣不成聲的鐵的歷史教訓啊?!這些反動罪惡的暴君啊,倘若他們的心靈深處稍為民哀所系,為何在那惡夢乍起處,不冷靜地深思一下天下百姓的民生之難、積貧積弱的切膚之痛呢?如果是這樣,他們怎會如此饕餮地揮霍民權而最終又使天民作為犧牲代價去替他們因無知亂政、暴殄天物地代復一代地白白殉葬呢???——偉大的“詩圣杜甫”之所以能成為不朽,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委那就是,他將觀察人民之苦作為天職、吶喊人民之痛作為使命!然則,在這同一種意義上,早在戰國末期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在觀察民情、民生、民苦上同樣有其深刻的思想詮釋和藝術再現。毋庸深究屈原全部作品,這里僅就其《離騷》一篇就可洞察其遠大的治國抱負、濃厚的愛民情感、洪廓的治國理想以及深徹的舉賢任能、修明法度的政治主張。《離騷》雖則由敘述身世、出生、為政、遭讒命運及憤世嫉俗之苦到最后在因“美政”遭遇玷污而終止生命為止,其實,透過他《離騷》深沉而委婉的敘述,聰明的讀者不難想象其深邃之核心思想便是“舉賢薦能”與“福祜天民”;這是屈原多么超然物外的世界觀啊!
然而,兩千多年來,人民在研究這部偉大而不朽的作品《離騷》時,居然忽略了一個極其嚴謹的人文問題:如果說屈原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不如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愛民詩人”更為精確。為何?——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天下的人民遭遇生靈涂炭,周土狼煙四起,國破家亡,亂臣賊子顛覆朝政,昏庸的暴君將國運引向覆亡;請問,爾等大勢西去的腐朽大廈和黑暗的政治集團所媾和成的禍殃之國有何值得愛惜的呢?論及屈原“愛國”,其實不就是在于他憐憫天下倍遭踐踏的勞苦大眾的么?他在寫完《懷沙》之前,遙望遠處天邊的故土:那里的兄弟姐妹在苦難和貧窮里掙扎;那里的親朋好友在悵惘里彷徨;那里的長輩嫛婗在亂世里期盼;那里的生靈在窒息的空氣里低回;那里的被劫難的亂臣賊子及臭氣熏蒸的朋黨因失去了昏君而不知所措地東躲西藏。……總之,楚國全境陷入了被秦國征報的莫大的恐懼與無限的恥辱之中!請問,偉大的、將以死殉國的屈原他不在愛憐那些可憐的人民還在可憐誰呢?!這些在《離騷》均有記載;詩中這樣寫道: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這是說屈原常常自拭淚水,那是因為勞苦大眾多災多難的原故啊!自己只是愛惜節操,可是早上諫言晚上就被罷了官。在這清晰的字里行間里,人們不難看出屈原堅定不移為民申訴、為民請愿的矢志不渝的堅強決心。他繼續陳述說: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屈公說,為了自己所鐘愛的民情,即使是面臨九死一生也不會有悔意!因此可見,那時的屈原在楚懷王面前反映勞苦大眾的不幸,在多大程度上觸及了昏君及朋黨罪惡的靈魂啊!否則,那些黑暗政治集團為何這般痛恨他呢?因為他的美政撼動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因為他的覺醒意志時刻都在燃燒正義的火種;相形之下,那些作惡多端的反動派哪有甘心受辱呢的?然而,在《離騷》第八部分的尾聲他這樣尖銳地總結道:
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屈公是在警醒世人:人們應以史為鑒去把握事物,要觀察和研究人民最需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在田野上怎能讓豺狼去放羊呢?要治好國家又怎能讓罪人和惡人去稱王的呢?可想而知,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屈原以極其樸素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總結出了治國、清政如放牧一樣的科學圭臬,這是多么偉大而科學的政治主張及人文情懷啊!雖則時過境遷,朝代不斷在更替,然而,延展迄今的農耕文明又給世人以怎樣的思想恪印和啟迪呢?
三十年前的廣大農村現狀,又是怎樣的令農民苦難不堪的訴說著他們內心深處的悲傷呢?那時,筆者的孩子才六七歲,被寄養在家鄉但店深山的一位伯母家。這年深秋筆者回鄉探訪老人和孩子。那幾天,身受感同地體驗了農父饑餓、逃荒、稅賦、征糧以及基層官員請功邀賞、魚肉百姓之事屢見不鮮。遂然,創作了諷喻詩《秋收》。詩中筆者這樣寫道:
人均三五分,周土逃饑荒。
四季難糊口,終年嚇稅糧。
這里的人民平均三五分土地,青黃不接時,只得外出討荒(討米、討飯、要飯)。他們長年食不果腹,還要忍饑挨餓地向政府繳納相應數量的各種稅賦。這樣驚嚇的日子怎讓人民不四處流離、背井離鄉呢?接著筆者寫道:
斷有富足家,巧施文采賬。
來年償新谷,翻息肖餓狼!
小斗借出來,大戽收回倉。
田家處當代,佃戶安古狂?
筆者告訴人們,即使偶爾有較為富足之大戶人家,但他卻象當年劉文彩時代以收貸的手段來剝削窮苦人家:“小斗借出來,大戽收回倉。”人們不僅思考;為何事情發生在當代,居然怎會存在像古代那樣瘋狂地人吃人的惡行呢?筆者接著諷刺地描述道:
農父敲糧局,官府應邀賞。
畝產過千斤,大會正頒獎!
天下不借米,國中有余糧。
稍有良知的人無不因此而噴飯:農民一邊在借糧償還高利貸,一邊又要接受官府大唱高調“畝產過千斤”的“大會正頒獎。”如此嚴重性的社會矛盾和弄虛作假的地方狗官,他們在為誰執政呢?這些狗官又是怎樣替國家和天民作為的呢?在《秋收》的尾聲,筆者這樣質疑道:
小媳嬌兒歸,羸弱病膏肓。
甑爨朽塵影,夫鄰討天鄉!
秋收歲歲序,春宵代代涼。
農耕無限苦,野人有何方?
是說出外討荒的媳婦帶著幼兒她們骨瘦如柴在深秋歸來,灶臺上堆滿了塵埃卻又不知丈夫從鄰村出去后的音信。雖是秋收季節,人們總是在這個節令外出“討米”以賑春天的饑餓。他們年年這般飽受著饑饉但如果不這樣復制糊口又怎能解決這必不可少的稅賦與饑荒的窮途末路呢?這是二十世紀80年代筆者所親歷的農村現狀。與此同時,筆者再將歷史向前推30年,在他的悲愴歌詞《苦將行十七拍》里,讀者們將目睹另一幅凄愴的鄉村畫圖;筆者這樣刻畫道:
公兮插桿復坐船,欲言與兮在口邊。
頓訴官兮瓶罄罍恥不作為,
問我何兮耕讀詩書放長天!
我復聞兮將蹲下,惺惺依兮扶穩船。
長老喟兮我生命,聲聲惻惻我兄遭難:
“汝兄孫兮名建國,十三勞分遂輟學。
日工分兮“四分半”,貼補家兮寬父母,
十八戀兮申家女,蝸居寒兮無婚處!
適有伯兮求遷徙,去往州兮改善居。”
20世紀70年代中期,筆者全家因祖籍尋親而回歸黃州陶店。76年夏天,筆者長兄建國因原居故土浠水蘭溪方鋪難以安身棲住,遂于夏天先一步遷往祖籍。而父母等在深冬陸續回遷;筆者卻在當年底孤人尋跡一年前曾經到過的浠黃渡口。因為半年前長兄建國同艄公一起論及其故土方鋪的危難處境,這回艄公便全然講給筆者并令筆者記憶猶新。這里,僅通過《苦將行十七拍》艄公重溫長兄之苦一章節以反映那個時代政治之昏聵、制度之腐朽而導致人民離鄉背井、遠征祖籍、飽受艱磨的社會寫照。關于筆者全家辭水如州前前后后之悲鳴傷痛、飽受磨難等不幸在不少作品均有再現。這里論述的諷喻詩《秋收》及《苦將行十七拍》,其嚴肅的中心主題,便深度凸顯筆者文藝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政治主張與人文情懷。……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當天下人民飽受苦難,且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時,那所謂視而不見、草菅人命的罪惡的政府就不應該退出歷史舞臺或被徹底打倒嗎???人類的農耕文明發展迄今,那些桎梏于勞苦大眾身上的“鐵鏈手銬”難道就不該“砸碎嗎?”誠然,筆者將自己置于農村現實的大環境中——使親歷親為的感同身受與耳聞目睹的時代變遷血淋淋地陳述在廣大讀者眼前,這無異將讀者與作者擺在了同一個極其嚴肅的社會命題面前:詩人、作家及一切文藝家等,其謂之擔當、言之使命、俸祿以國、根植以民,這“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最終該為誰而“詩”和為誰而“歌”呢???……
毋庸置疑,詩人、作家等當必須為天民而歌、為偉大的歷史的創造者而歌、為普天下的勞苦大眾而歌!故,《尚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
也就是說,詩當表達作者的遠大志向和思想抱負;歌辭(包括音樂),乃使人們知道其深邃的難以忘懷(長久)的精神內涵。因此“詩歌”自《詩經》以來,就注定當以承載詩人、作家等對人類歷史的創造者——廣大的勞苦大眾改天換地、開疆拓土的革命精神和不畏強權及暴政的歷史使命!在人類歷史長河里,偉大的人民,他們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大廈勛業,同時還為后世總結出了千千萬萬基于科學治國、循法治世、尚理治亂的不朽洪范。然而,盡管如此,人民在經歷巨痛的開國之后,總免不了那些“亡國之君”不孝先王、驕奢淫逸、朝秦暮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暴政橫起、草菅人命、目無天民、荒蕪國政、醉生夢死、昏聵無能以至于庶黎涂炭,水深火熱之悲劇每每重演!這——就必須由天下敢作敢為的類似白居易、李紳、杜甫、屈原等詩人、作家那樣奮然拿起投槍和匕首:以“美刺”之法度呈現“驚天地,泣鬼神”之作,使那些昏君們得以警醒;讓那些佞頑惡小深感罪責難逃;使天下的勞苦大眾覺著這個世界最終還有人為他們說話、為他們鳴不平!這——就是道德的重塑、人文的自覺、正義的力量!作為詩人、作家等,不仰仗手中的工具為夢想揚帆、為生民吶喊、為時代放歌、為橫征暴斂的統治集團投擲“投槍”和“匕首”,那么,國家和人民養育這些無病呻吟、“見死不救”、尸位素餐、茍且偷生之文人又有何益?……
如果說前面論及的“詩言志,歌永言”乃詩人(包括一切文藝工作者)職業操守之規范的話,那么,開篇論及的“美刺”及“文以載道”則是詩人、作家等這一特殊行業之責任與使命耳!
2019 年 8 月 17 日北京轉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