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綜,又引眾怒了。
前不久,一檔主打傳統文化的國風綜藝,被上萬網友群嘲出圈。

因其魔改《紅樓夢》,女性角色人設崩壞。
林黛玉成了嬌妻文學代言人。
「在這個大觀園里,我就是最沒用的。但寶玉也不需要我有用,我就美美地來,美美地走。」

探春成了恨嫁女。
「難道說,我要嫁給王孫公子了?這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正房生的。」

寶釵則成了精致利己的心機女。
「既然不能嫁給皇上,那也要選一個富貴男子嫁了才行。」

愛抖機靈,自夸長得漂亮:
「有沒有情和動不動人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動人是因為我長得動人。」
殊不知原著里寫道寶姑娘「有幾樣世上的人沒有的好處,模樣兒還在其次」。

更令人窒息的是男性角色。
他們坐在一旁評頭論足,張口就是這個女子「值不值得娶」,個頂個的油膩。
活生生拍了一出「東八區的紅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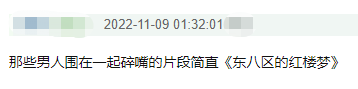
憤憤不平的網友們給節目怒刷一星,甚至舉報要求下架。
直接令評分從9.0跌到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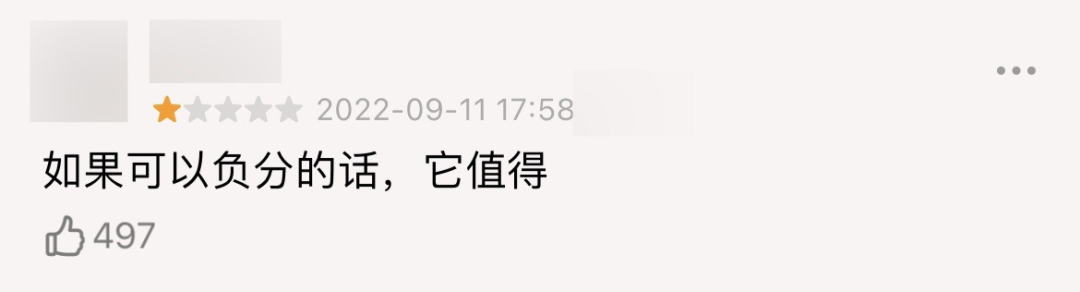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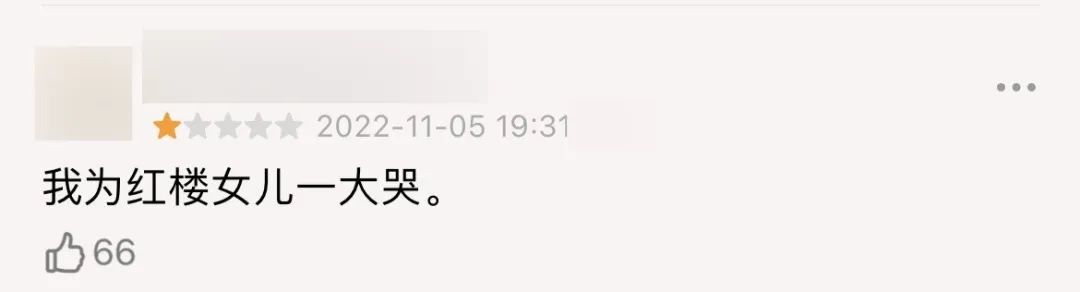
這幾年,「國風」已然成為內娛新流量密碼。
但用新形式演繹古典文化,很容易踩雷翻車。
好的國風節目應該是怎樣的?
有一檔紀錄片,就贏得了一致的好評。
第一季剛獲得金鷹獎最佳電視紀錄片獎。
第二季收官后依然穩定在豆瓣8.8分,堪稱今年的國風范本——
《中國》第二季


這套紀錄片和翻車的國綜一樣,都由演員演繹古代人物。
也同樣在「美」上下了大功夫。
畫面構圖精巧,富有意境之美。
小橋流水、竹林掩映的中式景觀,幀幀如畫。


可僅僅有面子還不夠,更關鍵的是里子。
《美好年華研習社》翻車的《紅樓夢》一期,便是徒有其表。
用舞臺劇的形式,對金陵十二釵的花名簽橋段進行解構,卻完全矮化了原作的女性群像。
相比之下,這部紀錄片則還原了古典名著的格局。
真正在通過現代的演繹,為古代女性發聲。
它借關漢卿的故事和作品,共情了那個時代的女性。
瓦舍勾欄里,不乏有出色的歌姬,數量也遠高于同時代的男藝人。
但卻鮮少有人關注,名字只集結在一本小小的《青樓集》中。

有的即便得到關注,但也無關她的能力和作品。
比如珠簾秀。
她是一名優秀的戲曲演員。
不僅能歌善舞,還能舞文弄墨。
但旁人關注最多的只有她和關漢卿的緋聞,好奇她為何拋棄關漢卿,轉而和一個無名無姓的錢塘道士結婚。

不僅才華得不到社會認可,她們還面臨著皇權和夫權的雙重壓迫。
有的歌姬會突然被官兵抓走,然后就再也回不來了。
還有很多普通女性被丈夫當成貨品一樣販賣。
她們始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目睹此情此景的關漢卿,決定用創作替女性伸張正義,讓女性可以通過努力追尋自己的幸福,改變自己的命運。
「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實的痛,直截了當地喊出來。」
于是,才有了《竇娥冤》《救風塵》《西廂記》這樣的作品。

其中,《竇娥冤》是大悲之作,也更生動地體現了那個時代女性的艱難。
無辜的竇娥不斷遭到欺壓。
先是被父親賣給別人,成為童養媳。
丈夫死后,又被膽小怕事的婆婆逼著改嫁。
還被潑皮無賴誣告,慘遭酷刑折磨。
在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真真正正為竇娥著想的,也沒有人會聽竇娥發出的聲音。
絕望的她只能寄托鬼神。
可看似天地聽見了她的冤屈,但依然沒有改變凄涼的底色。
因為她的冤魂剛到父親那兒,就受到了指責。
「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
原來父親是害怕被連累,才來主持公道的。
這便是古代女性的悲慘境遇,有一種無力回天的絕望感。

而節目組則忠于原著,更強化了這一層表達。
在白茫茫的大雪之中,只有竇娥一個人在空中起舞,發出自己的控訴。
既悲壯又凄美。


《中國》的格局,不只體現在女性意識。
還在于對儒家思想的闡釋。
去年,《茲山魚譜》上映時,有許多網友表示可惜。
因為片中出現的漢字、各種儒學經典都是我們熟悉的元素。
故事也依托于大眾熟知的「貶官文化」。
但沒想到,這個本應該由我們拍出來的題材被韓國搶先了。

而這部紀錄片,恰恰拍出了一則貶官寓言。
海瑞和電影主角一樣,受到被貶文官的熏陶。
也立志要成為國家棟梁,而不是偽善的「德之賊者」。

而不同于電影主角看到官場黑暗后出世的想法,海瑞選擇入世。
他勇于抗爭。
在權勢極大的巡按御史巡防的時候。
其他人紛紛低頭跪拜,但身為學官的海瑞卻不。
「這里是教書育人的學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
他不計后果,不論代價,勢要整頓趨炎附勢的官場風氣。
相信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足以對抗官場黑暗。
之后,海瑞的官越做越大,更深感國家的岌岌可危。
但他并沒有獨善其身,而是決心死諫,「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事治安」。
在把家人托付給朋友之后。
海瑞就寫下了一份言辭激烈的奏疏,批判官場腐敗和皇帝的昏庸無道,竟二十多年沒有上過朝。
然后抱著必死的決心,抬棺上書。

奏章被皇帝看到后,海瑞不出意料地惹得皇上大怒。
盡管幸免于死,但還是被送進了監獄。
所幸,不久后,嘉靖皇帝去世,海瑞遇到了大赦,才被釋放。

回歸官場后,海瑞依然保持著清廉剛正的準則。
他也因此備受排擠。
每到一處后,都會導致許多不愿與他共事的官員自動辭職。
因此,他不得不輾轉于各個地方,沒有辦法好好治理。
最終,只能選擇辭官還鄉。

在之后的十五年間,海瑞一直沒有重新復職。
但對于建設國家的渴望卻從未消失。
他的信念支撐他忍耐所有的寂寞和不甘。

直到在72歲這一年,海瑞重新得到朝廷的重視。
這時的他發現官場風氣并沒有好轉。
「以他的道德標準,明朝幾乎沒有一個合格的臣子。」
但也更感受到自己的無力。
垂垂老矣的他已經時日無多了。
可依然沒有離開,而是決定效仿古人尸諫,希望用自己的死來喚醒蒙塵的國家。

這場殉道,比《茲山魚譜》更多了一分悲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不言自明。

比起傳統的歷史再現,當下流行的「國風」強調的是一個「新」字。
但創新拿捏不當,便是冒犯。
《美好年華研習社》就是一個例子。
前期之所以收獲好評,正因為它挖掘了歷史上被忽略的女性。
首集當中,漢代才女班婕妤化身漢服大秀的主持人。
從服飾形制的流變里,觀察到女裝追求腰細,而男裝未有同樣的設計。
對此,班婕妤脫口辣評:
「你們男人何時苛待過自己?」

現代臺詞、批判精神與傳統文化,巧妙地融合。
這是成功的創新。
再到《紅樓夢》一期,用新媒體裝置呈現太虛幻境,用舞臺劇、流行歌曲形式演繹十二金釵。
這些形式,其實都沒有問題。
87版《紅樓夢》化裝設計楊樹云老師操刀的妝造,也十分精致。
可一旦深入到人物塑造上,就露了怯。
不僅臺詞幼稚,內核也全面降級,失去了對封建悲劇、女性命運的批判和悲憫。
問題究竟出在哪?
我們把今年幾場爭議放在一起,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改編自關漢卿原著的《夢華錄》當中,花魁認為「以色侍人才叫賤」;
余華小說《兄弟》的觀后感中,有人大呼「避雷」;
《紅樓夢》主題節目中,十二金釵不符合人物個性的臺詞……

這些例子,無不讓人感到一種語言表達上的匱乏。
好像離開了網絡流行語,不抖機靈造幾個「金句」,就不會說話了。
說到底,綜藝的翻車,無法歸咎于個體。
也與整體越來越退行的知識環境有關。
正像劉擎老師在《十三邀》上指出的。
現在的成年人正在童稚化。
短平快的奶頭樂代替了深度閱讀體驗。
「在豐富當中變得貧乏。」
創作者不會再像87版《紅樓夢》劇組那樣,花費幾年的時間去研習原著、揣摩人物。
取而代之的是標簽化、符號化的人物,幾句自以為幽默的俏皮話。
「我就美美地來,美美地走。」
「真的沒人欣賞無用之美嗎?那我為什么這么紅。」
「什么葬花,還不是做給寶玉看的。」
以及用來炸場的「絕美妝造」。

哪還有什么《紅樓夢》原著精神。
就算寶玉黛玉的名字被替換成大壯小美,也沒什么違和感。
而更諷刺的是,節目彈幕被幾位流量主演的名字刷屏。
似乎粉絲們根本就不在乎經典被毀。
87版到綜藝版的《紅樓夢》,是從藝術創作思維到短視頻思維的降級。
作品的格局,當然小了。
反觀《中國》,格局之大正依托于創新的分寸。
不魔改,只解讀。
包括新的視角。
正如講述閉關鎖國政策的那一集。
想必大家都在教科書里讀到過定論。
而片中,拍出了更不為人知的乾隆內心的權衡和考量。
突破既定模式,自然讓我們看到了更立體的歷史。

還有新穎的人物塑造。
康熙擒鰲拜時,有這樣一場內心戲。
康熙緩緩走向已經被死死壓制住的鰲拜。
臉上的肌肉微微顫動,呼吸粗重,喉嚨吞咽著。
沒有臺詞,卻可感受到他心中難以按捺的激動。
不同于常見的對皇帝沉穩的刻畫,反而演繹出了獨屬于少年天子的青澀。

除此之外,一些設計也非常巧妙。
比如讓關漢卿遇見南宋的朱熹和張栻,和他們一起談論儒家思想。
這種方式模糊了時間、地理、身份的局限,讓人更能直觀地看到關漢卿對儒家思想的向往和郁郁不得志的遺憾,有一種獨特的況味。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當然值得被一再挖掘、解讀。
然而,層出不窮的翻車、魔改,已然背離了初衷。
流量明星參演的國風綜藝,每期播放量動輒上億。
翻車風波反倒令它在網上黑紅出圈。

可《中國》這樣踏實低調的片子,卻還有許多人尚未知曉。
對比之下,更令人感到可惜。
無論如何,重溫經典是為了讓我們摒棄浮躁,得到提升。
而不是強行將其降級,與快餐文化共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