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艾倫·柏狄克
摘編丨董牧孜
某些時間感知問題還是讓人疑惑不解,其中就包括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什么隨著年齡的增長,人會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在關于時間的所有謎題中,這可能是最常見、最基本也是最讓人困惑的問題。
在多項研究中,80% 的被試者表示年齡增長確實使得時間變快了。“我們變老了,相同的時間間隔卻變短了—也就是說每天、每月和每年都變短了。”威廉 · 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中這樣寫著,“小時是否縮短了還有待考證,但分鐘和秒鐘都保持未變。”不過,時間真的隨著年齡增長而加快流逝了嗎?像往常一樣,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對“時間”的界定。
“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韋爾登說,“人們說的時間變快了,到底指的是什么?癥結在哪里?僅僅因為某些人認為時間變快了,或者你提出問題:年齡增長是否使得時間加速流逝?他們回答說‘是啊,確實變快了’,而這并不能證明他們是對的。因為什么事情都會有人持贊同的觀點。事實上,這是個尚未進行探索的問題。我們需要找到恰當的實驗工具記錄現實生活,才能找到切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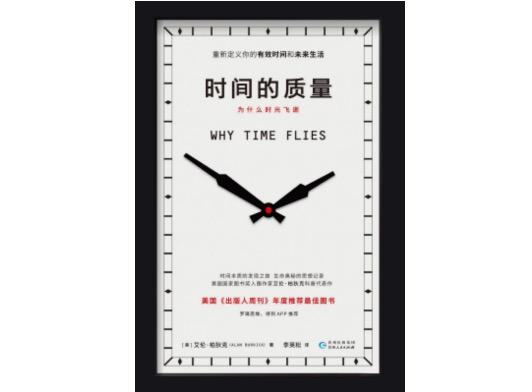
《時間的質量》, [美] 艾倫·柏狄克 著,李英松 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為什么我們對青春時光的記憶,比其他時期的更清晰?
時間—年齡的謎題至少有兩種表達方式。最常見的是對一段既定的時間跨度的表達:現在的你會認為這段跨度比你年輕時過得快。例如,你在 40 歲時的一年,比你在 10 歲或 20 歲時的一年過得要快。
詹姆斯援引巴黎大學的哲學家保羅·珍妮特
(Paul Janet)
的言論:“任何人在數算自己記憶中的 5 年時,最終都會發現,最近的這 5 年要比之前同樣的 5 年過得快得多。大家追憶自己最后8 年或 10 年的學校時光時,會說漫長得像一個世紀;而回憶人生中最近 8 年或10 年,則會說短暫得仿佛一個小時。”
在闡述印象方面,珍妮特提出一個數學準則:既定時間跨度的長度與年齡成反比。50 歲中年人對一年的時長感受,可能是 10 歲兒童的五分之一。因為一年是前者生命的五十分之一,同時是后者的十分之一。珍妮特對時間為何隨年齡的增長而加速流逝的解釋,帶動一系列相類似的理論出現,統稱為比例理論
(ratio theories)
。
1975 年,辛辛那提大學退休的化學工程教授羅伯特·列姆利奇
(Robert Lemlich,他可能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工業流程泡沫分離技術的研發人之一,該技術借助流動的泡沫清除液體中的污染物)
對珍妮特準則稍加改動,他提出,對一段時間跨度的主觀判斷與年齡的平方根成反比。
列姆利奇開展了一項實驗。他召集 31 名工程系學生
(平均年齡 20 歲)
和教職人員
(平均年齡 44 歲)
,要求他們以現在為出發點,對比自己人生中的兩個階段,評估時間流逝的快慢程度:這兩個人生階段分別是處在當前年齡的一半時和處在當前年齡的四分之一時。幾乎所有人都反映,與兩個以往人生階段相比,現在的時間流逝得更快。幾年后,馬尼托巴省布蘭登大學的心理學家詹姆斯 · 瓦爾克
(James Walker)
通過實驗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實驗中,他問一組年紀較大的學生
(平均年齡 29 歲)
,與他們處于當前年齡的一半時或四分之一時相比,“現在一年的長度有何變化”。結果 74% 受訪者認為年幼時的時間過得更慢些。1983—1991 年,北阿拉巴馬大學的心理學家查爾斯 · 朱伯特
(Charles Joubert)
曾開展過三項更具可比性的研究,紛紛驗證了珍妮特和列姆利奇的結論。
這種方法存在的問題是對人類記憶持有過于樂觀的態度。我連上周三中午吃的什么都記不清,更無從將其與之前的周三午餐做比較。因此,我怎么可能準確回想 10 年、20 年或 40 年之前更為抽象的體驗,即時間的流逝速度?另外,詹姆斯也曾提到,比例理論并未說明問題:珍妮特的提法“大致闡明了一種現象”,他寫道,但“并不能說揭開了謎團”。詹姆斯認為,時間隨年齡增長而加快的感受更可能緣于“回首往事的簡單化特點”。
我們年輕時,幾乎所有感受和經驗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能歷久彌新。隨著我們長大成人,習慣和例行事物逐漸成為行為范式,新奇體驗越來越少
(都已歷經滄桑)
,也就很少在意當下經歷的時間了。最終,詹姆斯寫道:“當我們驀然回首時,無數的日日夜夜早已一去無影蹤,那些歲歲年年也如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般成了斷瓦殘垣。”
詹姆斯這種陰郁的觀點與約翰 · 洛克的主張同屬于記憶理論范疇,洛克曾表示:我們判斷一段過去的時間跨度的持續時長時,依據的是發生在其中且被我們記住的事件數量。一段記憶滿滿的時光,流逝的速度會相對緩慢;而平靜如水的日子則飛快流淌,讓人猝不及防。記憶可以從多個角度對時間流速造成影響。情感經歷常常在記憶中占較大比重,因此對于一位疲憊不堪的家長來說,你上中學的 4 年—第一次參加畢業舞會、購入第一輛車、中學畢業,以及剪貼簿和照片中歷歷在目的難忘畫面—要比普通的 4 年顯得漫長許多;當然,比起你自己最近 4 年的生活
(疲于奔命和家庭瑣事)
,中學 4 年同樣顯得更加悠長。我們似乎會記住特定的生活階段,尤其是青春期和二十幾歲,對這段時光的記憶比其他時期的更清晰,這種現象叫作“懷舊性記憶上漲
(reminiscence bump)
”,可用于解釋為什么一段既定的時間會在過去顯得更長。

在美國電影《本杰明·巴頓奇事》中,男主人公生來像個老人,在長大的日子里逐漸“返老還童”。
以記憶為基礎的理論有這樣一種假設:我們長大后的生活會變得相對平淡。但這種假設不僅很難證實,還與日常生活經驗相沖突。在我的記憶中,遇見我妻子的那個夜晚比夏令營的初吻顯得更加清晰。雖然我記不清自己學會騎車時的天氣或年齡,但是我仍記著幾年前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六,那時我 46歲,在跟著自行車慢跑一段距離后,我松開了自行車座,看著 6 歲的兒子第一次獨自騎車,搖搖晃晃地穿過棒球場的草坪。在過去的 50 年間,我游歷過、愛過、迷失過,又重新來過,但越來越覺得早年記憶已不屬于自己或已歸還給了過去,所有重要的瞬間都發生在結婚生子之后。在這段時間里,我見證了兩個孩子的茁壯成長,他們認為新奇的事物讓我也從中有了“溫故知新”的體會:字母表、加法運算、乘法運算、“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是猶太人在逾越節家宴上的一種活動,旨在紀念神帶領他們出埃及。家宴開始時,由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以唱歌的形式提出四個問題,歌曲為 Ma Nishtana(意為“為什么今晚與平時不同?”)〕
,以及經過在庭院里的無數次訓練后,如何用左腳將皮球輕輕送入球門右上角的網窩?
時間好像確實提速了—當然,本來就很快—但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
是近幾年發生的事情比以往少嗎?抑或是發現孩子們的時間體驗沒有那么多緊迫和負擔,相比之下才顯得我的時間壓力更大?導致我的時間飛逝的原因絕不可能是由于缺少難忘的事,恰恰相反,可能是因為難忘的事太多,使我清晰意識到那些我想做但永遠不會有時間做的事情。隨著年齡增長,時間變快了,還是它其實一直以恒定的速度在流逝,只是因為我余年不多,所以感覺更珍貴?
在最早
(甚至早于列姆利奇)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中,有一篇 1961 年發表的研究論文,即《論年齡與主觀的時間速度》
(On Age and the Subjective Speed of Time)
,便是個很好的偽科學范例。研究人員注意到導致時間變快的一個要素是忙碌感。“忙碌本身就比較重要,”他們問道,“還是忙碌起來會使時間更有意義?”他們召集兩組被試者:118 名在校大學生和 160 名年齡在 66 ~ 75 歲的老年人。每名被試者手中持有一個列表,里面是需要分析的 25 個短語:
飛奔的騎士
逃跑的小偷
疾馳的巴士
高速行駛的火車
陀螺
吞噬一切的怪物
飛行中的鳥兒
飛行中的宇宙飛船
壯觀的瀑布
轉動的線軸
跨步向前的腳
旋轉的巨大車輪
沉悶的歌曲
揚沙
正在紡線的老奶奶
正在燃燒的蠟燭
一串珠子
發芽的葉子
手持拐杖的老頭
飄蕩的云朵
向上的樓梯
廣闊的天空
翻越山岡的路
平靜的海面
直布羅陀巨巖
被試者需要從“是否描繪出時間畫面”的角度考慮,將這些比喻短語分類,用“1”標注出效果最佳的 5 個短語,用“2”標注效果次之的 5 個短語,直至效果最差的 5 個短語
(用“5”標注)
。結果顯示,年輕人和老年人有著類似的時間體驗。兩組被試者均認為最具典型性的比喻是“疾馳的巴士”和“飛奔的騎士”等,而效果最差的短語是“平靜的海面”和“直布羅陀巨巖”等。然而,在經過一些額外的統計學操作后
(作為一名現代讀者,覺得有些可疑和費解)
,研究人員總結得出老年人更喜歡用動態的比喻形容自己的時間體驗,而年輕人則傾向于使用靜態的比喻。
不過,這項研究也暴露出方法論上的缺陷。作者曾研究過哪個因素—繁忙程度或對時間的珍惜程度—更能導致人們出現時間過快的體驗。研究人員對此做過詳盡的論述,認為如果是前者,那么應該是年輕人感覺時間加速了,因為他們比老年人更為活躍。但結果發現反映時間變快的是老年人,研究人員故此斷定:對時間的珍惜程度占比重更大,因為“留給老年人的時間不多了”。
然而,除了強調“老年人沒有年輕時忙碌和活躍”以外,作者并沒有對此進行論證。同時,對人們惜時程度的考量,所依據的僅僅是他們對時間修辭短語的排序。和其他許多試圖解釋時間為何隨年齡增長而變快的研究一樣,此項研究并沒有得出任何定論,基本屬于無用功。
為什么人感到厭煩時,會覺得時間很慢?
有一次,我受邀前往意大利,在一個專題研討會上做演講。我被安排最后一個發言,因此,整個下午我都在聽小組其他成員演講,他們用的都是意大利語,而我對此一竅不通。他們的話語讓我感到天旋地轉,有時,臺上似乎講了個笑話或是引用了至理名言,我表示贊賞地點點頭,仿佛聽懂了一般。我感覺自己就是太陽系黑暗邊緣中的冥王星,遙望著太陽的光輝,想象著要是能躋身其中該有多幸福。
當第四個或第五個發言人上臺時,我發現身前的桌子上面擺放著一副耳機,能夠將會議流程在意大利語和英語之間實現同聲傳譯,這時我突然發現后面角落中的玻璃房里有人在辛勤忙碌著。翻譯起了點作用,戴上耳機后,我知道了臺上這位發言人是名教育哲學家,正在將達爾文與牛頓物理學聯系在一起。也許是他延伸得太廣,也許是我學識太淺,或是兩者都有,翻譯開始跳線,出現大段的停頓,其間只聽到一位女譯員在費力地理順信息。我朝著玻璃房瞥了一眼,看到里面有兩個人。不一會兒,耳機中出現年輕男子的聲音,隨后意英翻譯變得更加快速、準確。
終于輪到我上臺了,觀眾席中只有兩三個人戴上耳機,其他聽眾讓我感到些許不安。我首先就自己不會意大利語向大家表示歉意,然后便開始了演講。
我故意放慢語速,想著能減輕譯員的負擔。但很快發現:語速放慢一半,意味著我只有一半的時間來完成 40 分鐘的演講。故此,我急忙進行現場編輯—跳過示例,省去轉接部分,砍掉整個思考過程,結果導致連我自己都不太明白自己口中所講的內容。戴耳機的幾位臉上的表情和不戴耳機的其他聽眾一樣,充滿了茫然和困惑。
1963 年,法國心理學家保羅 · 弗雷斯
(Paul Fraisse)
在《時間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Time)
中回顧了距當時一個世紀前后所有關于時間的研究,這是第一本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著作,從時序到客觀現時的感知長度,書中涵蓋了時間的所有方面。在考量無數項實驗之后,弗雷斯得出結論,說出“包含 20 ~ 25個音節的句子所需時間—至多是 5 秒鐘”。我個人的現時差不多也是這個長度。弗雷斯又補充道,我們對時間的大部分感覺和認知“均源自由時間造成的挫敗感,時間要么是在延緩我們現時欲望得到的滿足,要么就是在迫使我們預見現時歡樂的終點。因此,持續時間的感覺就來自對現時與未來的對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厭煩就是“因兩段持續時間
(你陷入的這段和你想要進入的另一段)
不重合而導致的感覺”。這是奧古斯丁“意識強度”的另一個版本,隨著我繼續演講,發現自己太過緊張了,我應該像太陽一樣把知識“照耀”給每一個聽眾。但我仍是那顆“冥王星”,太陽系里面的“行星”把望遠鏡都對準我,思考著如何處理這個遙遠、陌生又不茍言笑的對象。

美國電視科幻情景喜劇動畫《Rick and Morty》中,二人穿越時空。
當天晚上,在小組成員聚餐時,我見到了那位翻譯,他叫阿方斯,是一名語言學研究生,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葡萄牙語和英語。他又高又瘦,一頭深色頭發,戴著圓框眼鏡,儼然意大利版的哈利·波特。
我們都認為“同聲傳譯”純粹是一個矛盾體。不同的語言有著截然不同的句法和語序規則,所以無法逐字逐句地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譯者對聽者有所保留:譯者先聽取關鍵字或短語,并記在腦中,等待發言人隨后對其解釋,屆時譯者才開始大聲翻譯,此時發言人又繼續闡述新的字句和觀點。倘若譯者等待時間過長,就會面臨忘記原始短語或丟失正在進行部分的風險。雖然“同聲”意味著發生在現時中的行為,但實際上卻是對記憶的連續表達,這樣表達就明了多了。
翻譯來自不同語族的語言更具挑戰性,阿方斯說,比如德語譯成法語就難于意大利語譯成法語或德語譯成拉丁語。在德語和拉丁語中,動詞經常出現在句尾,因此譯者常常需要等到句子結束,才能開始翻譯。如果譯者翻譯的是法語,動詞一般會出現在句首,譯者可以選擇稍等下文,或可以猜測句子的走向。
聽阿方斯的講述,譯員像是奧古斯丁會認可的人—在過去與未來、記憶與預期之間來回拉扯。根據阿方斯的估計,譯員平均能承受 15 秒至 1 分鐘的滯后,即譯員聽到說話內容與做出“同聲”翻譯之間的時間差。譯員水平越高,能承受的滯后就越長,這意味著在產生譯文之前,能在頭腦中裝載更多的信息。譯員可能需要事先準備三四天,來熟悉即將面對的行業術語。阿方斯說,如果進展順利,同聲傳譯和沖浪很相似。
“你必須用盡可能少的時間思考詞語,”他說,“當你聽到一段韻律時,要隨著它流動。不要想著停下來,因為如果落后了,你就會失去時間,就會迷失。”
原作者丨艾倫·柏狄克
摘編及編輯丨董牧孜
校對丨盧茜






